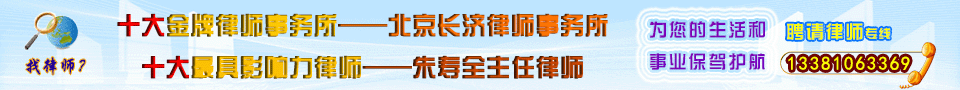八、风险代理案例
(一)该风险代理合同是否有效?
2002年1月14日,某律师所与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主要内容为:①某公司委托某律师所执行其与一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电子公司)货款纠纷一案,由某律师所指派律师刘某、肖某承办;
②某律师所代理执行范围包括电子公司欠某公司本金128万余元,诉讼费1.9万余元,因电子公司逾期付款产生的滞纳金。③某律师所代理的风险代理费数额为某公司申请法院执行标的额之己实际执行部分的15%……④法院执结数额不足20万元时,某律师所暂不收取代理费,执结数额超过20万元,而不足128万余元时,某律师所暂按执结款(含暂未收取代理费的20万元)的10%收取代理费,执结款达到128万余元后,一同补足该部分尚未支付的5%代理费,其余尚未执行部分将按法院实际执行数额的15%支付某律师所的代理费。⑤如果某公司同意与电子公司和解,某公司自愿放弃电子公司履行的部分,仍然按第三条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比例向某律师所支付代理费。……⑦某公司与电子公司经调解和解后,电子公司自动履行部分仍属风险代理的范围,某公司按第三条约定支付代理费。……⑨未得到执行部分某律师所不收取代理费。
按合同约定,某公司应支付某律师所法律服务费用26万余元。
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某律师所为某公司已追回执行款20.6万余元。某公司未向某律师所支付过代理费。
2003年8月13日,某公司与电子公司双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该案执行终结。原告某律师所要求某公司支付代理费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25万元。
被告某公司认为双方的约定不仅显失公平,而且也属无效条款,据此主张费用,理由不当。
[裁判要点]
法院认为该案系风险代理,收费标准由双方自己约定,各自承担风险,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该收费约定应受法律保护。判决被告某公司偿付原告某律师所法律服务费25万元。
[评析]
本案是一起新型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即所谓的风险代理,它是指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先不预支付代理费,费用先由代理人预先垫付,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无法收回预先垫付的费用;如果债权一旦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故称之为风险代理。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某律师所与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
根据合同有效的构成要件,当事人应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按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该风险代理符合委托代理全部形式要件,是典型的委托合同,而委托合同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不管报酬多少,只要双方自愿就不违反合同法,故应按有效合同处理。本案中,合同当事人双方都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都是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具体明确,已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如某公司与电子公司执行和解等,这些预见充分说明双方是基于各自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那么合同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目前,法律与行政法规并未针对律师风险代理收费有明确的规定,河南省司法厅根据司法部的规定出台了一个关于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该规定也涉及到了律师风险代理收费,但没有具体规定收费的比例及标准,只是规定依照当事人的约定计取。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当事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的财物”的规定是一项禁止性规定,而风险代理合同违反了这一规定,应是无效合同。本案中,与某公司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的是某律师所,并不是哪一名律师,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的禁止性规定是针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而言的,本案中维和律师所律师的风险代理行为均是由律师所授权而行使的,不存在“私自接受委托”的现象,应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而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从法律的制定机关来讲,《合同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而《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法律的位阶差别,从这一点讲,也应适用《合同法》。
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委托合同的全部形式要件,同时也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无疑是正确的。
文章《该风险代理合同是否有效?》作者: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文超 来源: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44936 2004-12-31 编辑:陈思
(二)风险代理中的报酬条款
1998年12月,原告(某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甲公司)的委托,担任被告诉乙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双方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合同文本系律师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约定代理费为“收回金额的15%,判决后一个月内给付”。原告依约履行代理事务。2001年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乙公司给付甲公司工程款9.6万元。甲公司不服,并且不听原告的劝说意见,提起上诉。二审中甲公司未委托原告为其代理诉讼。同年7月,二审法院依据乙公司提供的新证据,作出改判乙公司给付甲公司工程款1.3万元的终审判决。此后,原告因向甲公司催要代理费未果,遂于2001年11月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9.6万元的15%支付代理费。被告坚持按1.3万元为基准给付代理费。
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计算代理费的依据问题,审理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收回金额",应指甲公司胜诉后经乙公司履行判决或法院执行而实际取得的款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于代理费的金额,并未明确约定为一审判决金额的15%,由于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系由原告律师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不一致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第三种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律师所担任甲公司的一审诉讼代理人,而律师所事实上也仅担任甲公司的一审诉讼代理人,故律师所应就其代理的一审诉讼结果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本案原告应按9.6万元的15%获得代理报酬。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并分析如下:
1、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承认合同权利为自治权,意思自治是合同权利的本质属性。在一般诉讼代理的情形,律师所获取代理报酬通常是一案一计,一个诉讼程序阶段即为一个案件,一个诉讼倘若经历了一审、二审,则算作两个案件,若加上再审和执行,就算作四个案件。如果这几个案件各有代理人,则他们分别获得报酬,几个案件之间相互并无影响,实践中人们也未对这样给付代理费的方式提出过异议。这不仅是一个行业惯例或自由约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案一酬符合合同法上的公平原则,符合意思自治、责任自负的原则。
同样,在风险代理的情形中,如无特别约定,律师应对并且仅对其代理的诉讼程序阶段的结果负责,仍应按一案一酬的原则计付代理费。举一个反例或许更易理解,若甲、乙公司之间二审诉讼的判决数额大大高于一审判决数额,而律师所要求按二审结果获得代理报酬,这显然不能为合同法所认可。道理显而易见,一审代理人的报酬不能随着二审胜诉比例的扩大而增加,因为被代理人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利益并非一审代理人履行代理合同的结果。当事人如在二审中委托了风险代理人,其计付报酬时也不会考虑一审风险代理人的"功劳"而要求酌减二审代理人的报酬。
2、合同风险的合理负担
众所周知,诉讼风险存在于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即一审、二审、执行乃至再审等各程序阶段均有其风险,而代理人仅能控制其代理的程序阶段的事务范围内的风险,故律师所在委托合同中约定代理的程序阶段,构成了其权责范围、风险负担在时间向度上的边界(关于委托授权范围的约定则构成了空间向度上的边界)。而且,由于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并存,这个边界较之一般代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只要不是一审代理人继续代理,二审、执行乃至再审程序中的诉讼风险,不应由一审代理人承担。本案中,一审风险代理人即原告律师所恪尽职守,充分发挥诉辩机制的功能而获得较高的胜诉数额,乙公司已服判而甲公司不听律师所劝告,上诉后又未请原告律师所继续担任二审代理人,二审程序中客观实存的诉讼风险未获降低,终致胜诉数额大为缩小,该二审诉讼风险责任自然应由甲公司自行承担,而不能成为本案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风险的组成部分。
或许有人认为,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如此划分风险责任,未免过分夸大了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实际否定了生效判决的合法性、客观性。笔者以为,如前所述,在现今的诉讼机制中,当事人付出的诉讼成本多少,往往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而当事人选择风险代理的案件,往往又是此种影响更为显著的一些案件,因此,这些案件判决结果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一、二审判决可能出现的差别,实在是当事人可以预料的事情,并不存在欺诈、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尤为重要的是,风险代理的前提就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都承认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双方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慎重权衡之后作出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和约定,包括对提供代理服务的程序阶段的约定,应为合同法律所尊重。
3、格式条款应如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此条规定的前段和中段有一个衔接关系,即对格式条款先按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在有两种以上解释,也即有两种以上通常理解的,才应按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理解进行解释。因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制定,供现在及将来不特定的众多的交易时使用,具有为交易上的规范或制度的性质。所以,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应考虑到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和利益,应以该条款所预定适用的特定或不特定的消费者或顾客群的平均而合理的理解能力为基础进行解释,这种可能订约者的平均、合理的理解,就是“通常的理解”。对格式条款以“通常的理解”为标准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称之为“统一解释原则”。在格式条款有且只有一个符合合同法立法精神、可一贯适用的通常理解时,法院应依此解释,而不应先入为主地探求提供方的动机,责备其作为强势的熟业经营者为何当初不将条文含义完全写清楚;不应因为它是格式条款,订约双方对之理解出现争执,就直接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那只会导致格式条款在此案中是一种解释,在彼案中是另一种解释,而使合同条款的解释被不适当地用于贯彻单方的利益,从而违反“同类事项作同样处理”的民法原理。
本案中,当事人对“收回金额”有两种理解,但并非都是合理的“通常理解”。若理解为二审判决确定金额,则否定了意思自治原则与风险合理负担的规则,而被用来贯彻了委托人一方的单方利益。本案中的风险代理格式合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被用于多个诉讼代理事务中,委托人与他人的一、二审诉讼结果有多种情况,或一审高于二审,或二审高于一审,甚至更有委托人主张按再审或执行结果计付代理费。因此,本案格式条款的可能订约者的平均、合理的理解应当是:律师所代理完成的诉讼程序阶段的结果金额即“收回金额”。
文章《风险代理中的报酬条款》作者:人民法院报·周舜隆 来源: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_6/24/1619594988.htm
(三)律师风险代理费法庭上获得
上海凯昌律师事务所怎么也想不通,原本替上海某银行代理一起诉讼案件,双方约定了律师收费按照案件执行实际收回到账金额20%计付,可事后银行以其他理由称,不愿再付这笔费用,导致酿成了这起诉讼。近日,上海静安法院一审判决该银行需支付凯昌律师事务所报酬131.52万元。
2004年2月3日,凯昌律师事务所与该银行订立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凯昌律师事务所代理银行与汇丰发展公司、金帝建设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的诉讼一、二审及执行期间代理人。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吴律师为银行的代理人参与诉讼执行事宜,律师费依案件执行实际收回到账金额的20%计付,如被执行人破产或进行资产重组,通过分配破产财产或企业资产重组收回的款项不属受托方(律师事务所)收回款项,委托方(银行)对该部分款项不支付律师费。签约后,律师事务所指派吴律师参与代理案件的诉讼。
2004年10月,该银行在案件终审生效后,继续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吴律师,作为案件执行的代理人。同年12月,法院依法查封了金帝建设公司名下的股权,并向法院申领债权凭证。同日,法院通知金帝建设公司,拟对所查封的股权依法作评估,还向该银行出具了债权凭证。
2005年6月27日,该被告银行与金帝建设公司、汇丰发展公司等订立债务清偿协议书,确认法院生效判决书为偿还银行的债权,由金帝建设公司应向该银行偿付人民币822万元,在履行了该笔付款后,由银行再向原判决法院提出解封。同年7月13日,该银行向原判决法院出具申请书,表示已与被执行单位达成了债务清偿协议,与此同时,该银行还向法院出具变更授权委托书,撤消了原指定的吴律师的代理资格。该银行实际在2005年6月至12月间,该银行收到了人民币822万元。
一直没有拿到律师风险代理费的凯昌律师事务所,在2005年11月下旬,提出起诉将该银行告上法院称,该银行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律师风险代理合同,在律师履行了代理义务,在该银行实际收到上述钱款后,却不支付律师费,要求该银行偿付律师服务费164.4万元。
法庭上,该银行则辩称曾委托凯昌律师事务所为诉讼代理人,但在实际执行中律师仅向法院申领债权凭证,银行的债权还没有实现。之后,是银行自行与被执行人协商订立了“债权清偿协议书”,该行为的完成与律师无关,收到的款项属于被执行人资产重组款。按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该笔钱款不属于律师事务所代为收回的款项,那么作为银行则无需再向凯昌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
法院认为,凯昌律师事务所与该银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后,凯昌律师事务所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受托案件的一审诉讼及案件的执行。凯昌律师事务所在履行合同中不存在过错责任,该银行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报酬(即律师费)。尽管,该银行认为所收回的人民币822万元,是依据与被执行人订立的“债务清偿协议书”,
属被执行人资产重组后支付的款项,但在“债务清偿协议书”中并没有载明被执行人所付款系由于资产重组而致。相反该“债务清偿协议书”明确表示协议生效后,该银行同意法院中止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在被执行人履约后,由银行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的股权。由此可见,原审法院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均是凯昌律师事务所履行委托合同时所为。该银行实际收回的822万元,不应认定是因资产重组所获得。
那么,该银行变更授权委托,撤消原指派的吴律师作为代理人的资格,仍需向凯昌律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报酬。考虑到在审理过程中,凯昌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向法院举证说明,律师也履行过参与“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签订工作,对此应酌情扣除律师事务所应得的报酬,遂一审判决由该银行支付131.52万元。
文章《律师风险代理费法庭上获得》作者: 上海静安法院 李鸿光 来源:
http://www.justice.gov.cn/renda/node352/node3112/node3131/node3164/
userobject1ai928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