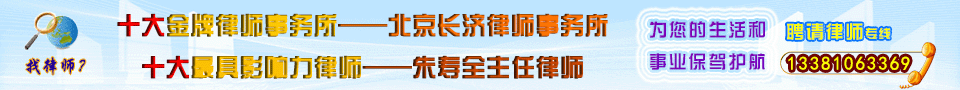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上海《东方早报》 杨耕身 2010-04-20
基层的治理之所以一味在“怪圈”里面打转,基层社会之所以疲弊难消,根源于一种政绩压力。一些官员仍笃定地认为,相对于稳定的“大好局面”,维稳的代价有多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其中提出: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准确评估社会形势才能从容应对;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容纳冲突,用制度解决问题等。(《中国青年报》4月19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名头,报告初稿撰写者晋军、应星、毕向阳,以及统稿者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之皇皇阵容,无不在为这份报告增加分量,让它显得更加让人瞩目。这样一种坚韧的努力异常可敬,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不免被一种倦怠的情绪击中。想一想吧:不论是“越维越不稳”之现状,还是所谓“新的维稳思路”,它们有什么是新的?要经过多少“维而不稳”的事实堆积,才足以让人总结出一个“维稳的怪圈”?而那些“维稳思路”,也早已是河上的桥。难道仅仅因为过河者总是选择去摸石头,所以它才成为新的?
一些地方“基层不高兴”的情绪已四处蔓延。对这样一种“不可治理状态”,身在社会中的人们,比之专家学者无疑有更深切的感知。那些维权者的苦难,他们的愤懑与怨气,承受与不可承受,不说也罢。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参与维稳者的压力与不甘。去年4月《半月谈》曾刊登一名乡镇信访工作干部的来信,他忧伤地写道,“自从分管信访,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这些维稳者与那些不稳定因素,既处于维稳工作的两端,也都成为体制“痼疾”之下的受害者。由此所展现的,正是一个早已疲惫不堪的基层社会现状。
基层的治理之所以一味在“怪圈”里面打转,基层社会之所以疲弊难消,根源于一种政绩压力。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吏治考核办法,于是当地方稳定成为 “一票否决”,从上到下都在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之时,地方政府不得不陷于穷于应付之困境中,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在维稳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一些官员仍笃定地认为,相对于稳定的“大好局面”,维稳的代价有多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且不论“稳定”已成为一些权力者滥权践法的借口,单就通常的“维稳”而言,它也只能使得地方政府为了一个稳定的假象而无暇他顾。它不仅使政府正常的守夜人职能、司法应有的“最后的公正”职能被虚置,而且也使得民众正常维权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在某种“同仇敌忾”之下,他们可能永远无法遇到可以说服的权力,民众的怨气也就在逐步郁积之中,成为基层社会各式各样的“火药桶”,一触即发。而由此带来的,又是新一轮的维稳压力与投入。这既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关键,亦是导致维稳工作陷入“越维稳越不稳”怪圈的深层原因。
民众的诉求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需要得到保障。当不能实现对于基层社会有效的治理,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厘清两个认识的时候了:到底是以权力训导权力,还是以权利驯服权力。以权力训导权力,指向的只能是权力的威权思想,而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使权力体系能够俯首于公民权利。因此,最终需要落实到对于体制的改革之上。如果说,旧的维稳思路纠缠着太多人治或权大于法的心结,那么改革就必须向体制中注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主灵魂。
当“稳定”成为一种高于人权、高于法治的追求或潜规则之时,其实已经表明疲弊的程度。“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依旧是参与报告统稿的孙立平先生曾经说过的,“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时,应该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只有充满自信的体制,才会有舒展,才会有自如的收放,才会有最根本的稳定。但是,对于信访,对于维稳,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