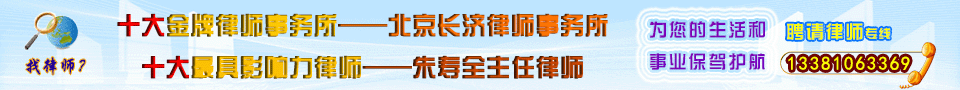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 刘畅
近日,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起刑点,仍然是使用1997年的5000元标准,而“一九九七年的五千元和二○○九年的五千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言下之意,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起刑点也应该提高。
他还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以此说明惩罚不均衡的问题。
好吧,他说的两点,都是有道理的。但道理分大小、有强弱,最终如果真的要做出一个决定(当然,一个最高法副院长,还没大到能做出这个决定),应该尽可能把各方面都考虑到,权衡利弊,再做定夺。
首先,让我来说说张军同志说的话的道理,以充分表明,我并不是看不到他所说的问题,也不是完全反对他的观点和事实。
1)关于起刑点的提高。
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2008年统计结果是300669亿,如果今年“保八”成功,那么2009年度至少是324722亿。和1997年相比,已经是41倍了。
实际上,1979年(当时GDP为4063亿)后,贪污贿赂犯罪的标准,从司法解释的1000元涨到了1997年的5000元(1997年的78973亿是1979年的19倍)。
我们把41和19简化成40和20,那么GDP成长20倍,就从1000元提高到5000元的话;则40倍情况下的调整,应该视作2个20倍,也就是从5000元先乘以5,再乘以2,也就如果定50000元起刑点,那么和之前1979到1997的提高幅度是类似的。如果我们能接受从1000元调整到5000元;那么从5000到50000,貌似也是可以尝试的。
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提高经济类犯罪的数额门槛,可以防止刑法的适用范围变相扩大、变相地向重刑主义靠拢。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2)关于惩罚不均衡。
也就是,有些小案子,公诉来法院的,法院按照标准必须判,但实践中很多更大的案子都没公诉。所以小案子可能判刑,而较大的案子又可能不移送,最终导致了惩罚的不均衡。而不均衡本身,就是对“平等性”的损害——众所周知,“平等性”是法律基本的原则之一。
但是当我们考虑了合理性和平等性之后,必须也要考虑其他问题。
【先来说说“合理性”的另一面】
贪污贿赂类的犯罪,并非单纯的财产犯罪,还复合了滥用职权的性质——实际上,我们主要反感的,也就是以权谋私这部分。
所以当我们合理地考虑了贪污所侵犯的财产数额标准是否过时时,理所当然也应该考虑贪污对财产之外的权益,造成的损失。对官方信誉的伤害、人民和政府的离间、作假账等掩饰手段导致的政府账目问题、财政不足导致的正常办公被拖累等等。
我们可以说,2009年的5000元钱,远远不及1997年的5000元钱值钱;相应的,现在侵犯5000元的财产权益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及1997年去侵犯5000元。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部分的刑法,已经不那么“罪责相适应”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的社会已经经过了80、90年代疯狂的下海淘金浪潮,在如今的经济基础之上,精神和政治层面的需求比之前那个年代强烈得多。
毛泽东逝世,江青的丈夫不再,粉碎四人帮,文革随即结束。之后几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理念上的分歧,以人民的选择结束。在精神上,主要是吸收外来文化和摆脱文革时期极“左”的影响,并且更重要的是开始重视和追求物质成果。
那个时候,主要是开放私有经济,很多人做农副产品、下海经商,甚至是走私、投机倒把。这些无论怎么看(也不论方法是否正确),肯定都是追求个人的发展、幸福。
但在经历了80年代的淘金浪潮、暴富和外来文化影响后(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文革中和文革后,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已经弱到和外来文化不在一个档次了),人们对精神和政治层面的追求被重新激活了——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反腐。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奴封资共,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人民的问题;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说是人神共愤又无可奈何,即便如朱元璋一般一次就下几万颗人头的订单,却也是“野火春风吹又生”。
腐败,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人民之敌,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共同的敌人——无论你是打算追求内心正义、还是有政治诉求。
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是官方正式称呼)平息之后,反腐被推到了更显眼的位置。这说明,全社会对腐败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90年代,新一轮下海经商的浪潮来了,伴随着的是贿赂又兴;同期国企改制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也不断暴露。反腐,更是到了举国重视的地步。
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宪政也好,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不能因为我们的敌人总喜欢打这些旗号,我们就耍性子故意不提它们。
而腐败问题,更是敌对势力攻击我国政府的口实之一,即便不谈腐败祸国殃民的问题,为了防御敌对势力的攻击,反腐也应该是重中之重。
实际上讽刺的是,“反腐”恰恰也是我国政府和敌对势力,没有太大分歧的事情——因为即便是我们的敌人,也会受到腐败的蚕食。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反腐的事情,都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所以,处理类似腐败类犯罪立法的问题,更要全面考虑。特别是作为最高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发言更应谨慎和全面,至少也捎带照顾一下民众感情。
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如此重视反腐的事情,腐败造成的政权公信力降低,更是必须被考虑的社会危害性。
想想看,如果副院长的这番话被片面地突出,我国政权就成了一个边喊“反腐”,边对腐败退让的形象了。更不用说,如果实际上发生了腐败问题,那更是伤害公信力、动摇政权基础。
我们可以计算通货膨胀,可以计算GDP发展,可以计算收入增长,我们可以就此提高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起刑点;但怎么计算人民和国家对反腐的重视和敏感的增长,这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如何增加?
【再说说“平等性”“均衡性”方面】
诚然,较小的贪污被公诉后判刑,而较大的贪污却没有移送,显而易见会导致刑法的不均衡和对不同贪污者的不平等对待。
在贪污贿赂这类犯罪中,公安对侦查、公诉都插不上手,完全是检察院运作。所以最高法副院长所说的不均衡性,可能是因为各地检察院宽严口径不一导致的,或者是为了效率和司法资源问题,有些地方只能搁置较小的案件。
只要不是检察院故意消极怠工、玩忽职守,那么这种口径不统一和对案件的取舍,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和副院长同志所说的“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一样,在北京贪污5000元和在青海贪污5000元,也不是一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宽严口径不同,是合理的表现。
而至于效率和取舍问题,显然同时有大小两个案件,人手又不足的话,选择较大的是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贪污腐败的金额常常惊人,这些地区检察机关的人员、设备也比较先进。如果不能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能力,就会出现拿着大炮打蚊子的问题。
不是说蚊子就可以不管,可是没那么多人手,只能向人大要预算要编制;如果有人说检察院消极怠工,那么我可要给检察院的同志喊喊冤了。就我所知,即便有纪委拿着“双规”到处帮检察院的忙,检察员们也是忙的四脚朝天——别忘了,除开反贪、反渎,检察员最基本的职责,还是大量普通案件的公诉(想想看每年得公诉多少盗抢这种普遍的刑事案件吧)。
退一步说,就算贪污贿赂类犯罪的均衡性的突破,有其不正确的一面,那么问题也是出在检察院侦查、公诉不力,各地查处的口径不统一,于法院何干?
法院和检察院是平行的司法部门,人家检察院自己都没说什么,最高法院一个副院长有什么好说的?除非他是想指责检察院反腐不均衡,又不方便直说,就捣鼓一个“起刑点”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
起刑点的提高,就好像为了追求平等、而损害正义。确实,只要把起刑点提高,那么起刑点以下的贪污者们,在刑法上就平等了。不会出现几千的小贪官被判,而较大的贪官却根本没被审判。
但我们需要这种平等吗?
就好像生下来10个孩子,9个正常,有1个是残疾——少一条腿。我们都知道以现在的科技,想要复原一条腿是很困难的,那么把另外9个也截掉一肢,就真平等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如果这就是平等的代价,我宁愿要不平等。
提高起刑点也一样,小贪官和较大的贪官平等了,但平等了又如何呢?这不仅是掩耳盗铃,更是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我们绝对不能为了平等,而放弃正义。
【最后】
最后,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提议。
众所周知在我国刑法中有这样一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无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标准的一刀切用词。使用这个措辞,一定是针对那些不能容忍的严重事情。
这个词在刑法中也确实只出现了这一次。
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国对毒品犯罪的惩罚力度是最大之一。在其他国家,常常是因为毒品犯罪牵扯了有组织犯罪或数量太大,才加以严处。
比如全世界泛滥的大麻,因为毒性和成瘾性就较其他毒品低,所以在很多国家都很普及(当然我是指“非法的普及”),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但在我们国家,按照刑法“无论”的强调,那么理论上说,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大麻,也一样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缓刑与否就不讨论了)。
相比较之下,诸如盗抢类普通犯罪,数额小、情节轻的,都是走治安处罚。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对毒品犯罪如此重视,实际上是有“鸦片战争”这个历史因素的。而鸦片战争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标志。
那么请想一想,如果我们对历史问题都如此耿耿于怀,为什么要忘记那么多被腐败掀翻的王呢?
如何反腐在本文暂且不论。但我想,刑法应该针对腐败类犯罪加一个“无论”。因为无论怎么看,毒品犯罪也不可能比腐败犯罪更严重。
有些犯罪可能永远禁绝不了、有一些案件可能永远查不清楚、有些正义和平等代价高昂根本无法承受,这是无奈的现实。但如果连面对它们的勇气和处理它们的态度都发生了退缩,那么情况只能每况愈下。
有些正确的事情,你可能永远无力完成,但不要因此就假装它是谬误,更不要掩耳盗铃。
>>返回守夜在瞭望塔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