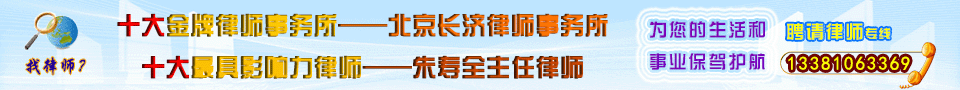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 刘畅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国家都有重刑主义的传统,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连坐、刑罚残酷繁重等等,都是重刑主义的表现形式。
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后,重刑变轻的趋势再明显不过了。人权保护、人道主义、无罪推定、更强大的辩护制度、更加完善的教育改造等等等等,都是在削弱重刑主义。
各位读者先不要着急,本文并不是无聊的宣传刑法人道主义,也不是看热闹、发泄心态的宣扬重刑主义。
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理论界更多的人倾向于轻刑主义,而民间显然普遍地对重刑主义更喜爱。而且因为一些具体案例,这两方观念不同经常会上升为更激烈的分歧、辩论直至最后的不欢而散。
但我看到,大部分人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到底应该重判还是轻判,仿佛把判决当成了最终目标。判决当然是非常重要,对于个案来说也确实就是最终目标了。但是当我们的讨论延续到“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时,显然不能单单看这两个主义。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问题,那就是刑事司法效果问题。如果说人权、人道主义和怜悯、仁慈这些高贵的品质,或者仅仅是追求国际趋势的态度,主导了那些倾向于轻刑主义的人士;那么,对刑事司法效果担忧的实用主义,则让另一些人倾向于重刑主义。
这里我必须先说一下“刑事司法效果”,真不好意思,弄了这么一个奇怪的词,这是我自己硬造的,要是我孤陋寡闻(我确实孤陋寡闻),学界有专门词语了,还请指出。
我所说的“刑事司法质量”,是包括了两点:能发现多少违法犯罪(因为很多违法、犯罪界限太模糊,所以我把违法也划入了);以及能解决其中的多少。
先说说解决的问题吧,比较好说。
在我国刑事领域,“命案必破”是公安内部的一种口号和指导精神,也是一种资源倾斜。“命案必破”保证了我国命案破案率从2004年至2008年的统计阶段,均达到了惊人的90%以上(新闻来源:中新网,2009年9月1日)。
我没什么兴趣说有些命案存在错案问题,比如那个倒霉的佘祥林,因为根本性错案、冤案的数量(只以我看到的来说)并不大,在纯粹的统计学上影响些微。就好像要发展道路交通,就必须忍受每年那么多的道路交通死亡(世界卫生组织09年6月的《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表示,每年有120万(本数字为中文版数据,英文版本为1.3million,相关详情可以查询世界卫生组织中文版网站和其上的英文链接))。
我要说的,从公安部公布的统计结果(公安部网站-政务公开-公安统计),我们可以查询到2003、2004、2005年的刑事领域的大致情况。
2003年是按不同类型的案件,统计了立案数量。虽然标题是“2003年分月侦查和破获刑事案件统计表”,但恕我近视眼,我真的没找到“破获”的数据。
2004年和2005年的倒是没问题。
2004年全年大约“侦查刑事案件”347.5万起;“破获刑事案件”103.3万起。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算下2005年的数字(不愿意查看的,我告诉你们,分别是374.8万和104.2万),数字也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国在那两年大致的破案率是30%以下。
各位一定不要误会,我无意冒犯我国公安的努力程度和刑事破案率,实际上我对刑事方面比一般人更了解,自然知道全世界普遍的刑事破案率都不高。
比如1996年时,统计后美国的破案率是20%上下,英国35%;日本在2002年也是20%上下。国际刑警组织或联合国的网站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国际统计。我外文实在太烂,所以只能给各位一些搜索来的老旧数据了~
不过看个大概意思足够了,这大概意思就是:“全世界刑事破案率,普遍不高”。考虑到我国巨大的人口和国土面积,以及经济尚不发达,所以传统治安刑事案件肯定多(如果都是金融类案件,那么立案数量反而可能降低),能有现在的成绩实属不易。经济不发达除了带来更多的小却多的案件外,还降低了公安部门的侦破能力。当然我们也有诸如严格的户籍制度等有利条件(而美国人则有可怕的信用卡追查系统)。
各位可以多看看警察,特别是一线刑警的私生活状态(我可不是让你们偷窥人家隐私,我是说如果你们认识类似熟人的话,或者从新闻报道),就更能体谅他们了。
我说的有点儿远了,我们还是来说重刑主义和轻刑主义吧。
第一个问题是,刑法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
1)罚犯罪/消化难以控制的私下复仇;
2)靠永久或暂时剥夺罪犯的犯罪能力,保护社会;
3)慑任何潜在的犯罪倾向。
第二个问题是,在古代,我们为什么倾向重刑主义?是我们的祖先比较野蛮、原始、不文明和残忍吗?也许吧。但我能肯定,这至少不是唯一的理由。
我不妨把解决刑事案件抽象成一个乘法算式:
(总体案件数量 — 未被发现的案件) X 惩罚力度 = 刑事司法的效果
总体案件数量凡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就连估算都很成问题,未被发现的案件就更不用说了,要是能统计出来怎么还能叫“未被发现的案件”呢?
所以实际上这个公式是:
发现的案件并破获 X 惩罚力度 = 刑事司法的效果
我不深究该立案不立案、正在试点的刑事和解等等因素。
考虑到我前面说过的破案率问题,我们知道所有发现的案件中,能破获的是少数(当然有人会说,那些统计中未破获的,也许以后会破获;但我也要说,那些当年破获的,也有过去几年的案子,两者应该差距不大;同时,有些案件可能是同一伙人做的,立案时很多,但一破获后破获数也多)。而只有破获了的,才可以考虑惩罚力度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达到一定的刑事司法的效果,那要么提高刑事案件的破案率,要么就提高对那些能够确认犯罪的案件的惩罚力度。
也就是简单来说,发现、破案数量不足的,用质量(惩罚力度)补齐。
这就是重刑主义最理性的来源依据了。在古代,刑侦技术比现在可落后得多,想要达到一定的刑事司法效果,那么必须依靠很多现在看来残酷的方式:
1)“连坐”可以督促互相监督揭发,提高发现和破获案件的可能,同时对连坐中“不作为”者,提高了惩罚力度;
2)“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是单纯提高破获案件的可能性(当然,刑讯可能变相的提高了惩罚力度——还没定罪就开始惩罚了~);
3)“残酷的刑罚”则是提高惩罚力度,达到提高刑事司法的效果的目的。
这么看来,我们的重刑主义,就算是残忍和不人道的,至少也是合乎理性的。符合当时社会条件所能支持的侦破能力,以及社会安定所需要的刑事司法效果。
这其实也是现在轻刑主义越来越时兴的原因,技术提高后,如果只是要达到一定的刑事司法效果,那么技术带来的“发现的案件并破获”的提高,可以用来平衡降低惩罚力度。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现在轻刑主义的倾向,和自己所认为的仁慈、人道和高尚联系起来吗?也许吧,如果连想都不愿想,那可真是残忍到家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轻刑主义也好,重刑主义也好,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如学界这样主张轻刑主义的话,那么应该从提供轻刑主义可以发展的环境下手,而不是从改变大众的内在品质开始。
什么是轻刑主义适合的环境?
重刑主义最显著的,就好像上面所说的,就是在各个环节都增加了惩罚力度。轻刑主义,针对重刑主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惩罚力度的问题。现在我国很多争论的焦点,主要也不是无罪推定这些,而是惩罚力度的大小。
平民喜欢惩罚力度大,但是他们大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刑法最终的效果削弱。而要提高这个效果,并不是一定要提高惩罚力度。
比如畸形的低破案率和高惩罚度结合,那么犯罪人被抓就纯粹是“中彩票”的情况了。就好像大部分人买彩票不会真的在理性层面上指望中奖,在这种极端畸形的刑事司法环境下,犯罪也会更肆无忌惮,反正抓住的可能性和中彩票差不多。
或者换句话说,犯罪成本太低,会导致犯罪成为一本万利、低风险高收益的选择,这样自然不利于保护社会。
其实说到“犯罪成本”,我多说一句,犯罪成本其实也是被发现、被抓获、被处罚这几项合并起来。任何一项畸低,都会导致成本降低。所以说起“犯罪成本”不应该只是针对惩罚力度来谈。
如果要维持一定的刑事司法效果,单纯提高惩罚力度,那么投机、冒险的人会增加,蹲监狱和死亡,并非对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效果,总有不怕死的,铤而走险的。
当“发现并破获的案件”不足时,所有侥幸(也许不应该说侥幸)逃过的,多多少少都会被社会察觉(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检举),这样会发生“老实人不平衡”的问题。然后越来越多的老实人也开始冒险,社会整体风气开始恶化。这也就是刑事司法效果降低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然而,当“发现并破获的案件”提高后,惩罚力度的降低很可能被平衡掉,而不会带来刑事司法效果的降低。这也就是轻刑主义真正应该追求的——而不是一个低破案低惩罚的容忍犯罪型社会。
刑事司法就好像打扫房间,你总不可能把屋子的所有地方都打扫干净。一般来说打扫打扫表面就行了,边边角角、犄角旮旯、柜后床下都可能漏掉。但这些地方积累的灰尘、赃物,在打扫之后,其实会继续影响到打扫干净的地方(不相信的话,各位可以好好收拾一下屋子表面,然后大致计算一下脏到一定程度所需的时间;然后再彻底打扫一遍,哪怕不是使劲擦地、擦桌子,只要保证犄角旮旯都照顾到了,看看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延长了)。这就好像高压往低压流动一样,堆积的灰尘也会往干净地儿迁移。“发现和破获的案件”如果不够,那么隐藏的邪恶,就会往其他地方蔓延。
如果轻刑主义者总是注意惩罚力度方面,那只会让整个屋子无论表面还是暗角,全都满是灰尘。当我们能有效发现和破获的案件增加到一定程度,惩罚力度自然就会下降。
为什么“自然就会”?这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法律并不无限追求正义,它主要还是追求效率。
很多人看到我说了这么多,可能会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高发现高惩罚”的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选择如此的(当然类似秦国那种军事国,或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我相信高发现高惩罚是很可能的)。
因为一个社会不会无限制追求“刑事司法效果(或者你们可以说它是某种程度的正义)”。当社会普遍感到自身安全可以接受后,对“刑事司法效果”的追求动力就会降低。因为这种追求,需要高发现高惩罚的支持,而这两高,都需要社会成本支持——说白了就是钱,就是税金,人力物力GDP,等等等等。
我们愿意为了正义支付多少代价呢?你愿意为了抓一个偷你5000元的小偷,悬赏2000元吗?3000呢?5000?10000呢?正义有价、事事有价,而人通常们宁愿去买些其他东西,正义并不享有第一优先权。
实际上,如果在考虑到监禁的成本问题,那么在“发现和破获的案件”提高后,惩罚力度几乎必然下降(除非动不动就枪毙人)。
所以我说,不能简单地以人道、人权这些高尚的观念,来对待重刑主义或轻刑主义。最重要的,还是实用主义的“刑事司法效果”能否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的社会,最糟糕的就是变成“低发现低惩罚”的容忍犯罪型社会;而“高发现高惩罚”的管制型社会,仿佛也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比较合适;
而对正义和效率比较平衡的两种类型中,“低发现高惩罚”是更倾向于经济效率的,“高发现低惩罚”则更注重没有人能逃脱制裁。
当逃脱制裁的人越来越少时,社会对惩罚力度的要求反而会降低——你可以说是“见怪不怪”,或者“考虑到经济效率”;但可能是更简单的原因:人们对未被抓获者的愤怒,不会再迁怒到被抓获者身上了,因为未被抓获者减少了,愤怒降低了。
在刑事司法领域,最好的情况,也许就是不患寡(惩罚力度),而患不均(很多罪行没被发现、解决)。
然而可悲的是,想要达到这种社会效果,恐怕和现在学界力主的无罪推定、人权、人道、辩护等等,对提高案件被发现和破获的几率,貌似都没有帮助。
>>返回守夜在瞭望塔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