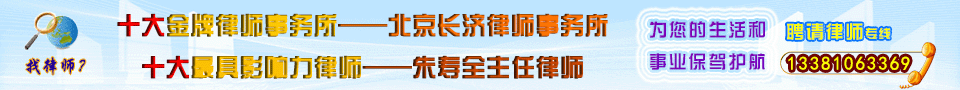政改的两条歧路
《在线律师》网特约撰稿人 杜蘅
增强党内民主与促进民众参与,或许是当下政改动向中最重要的两条思路。两条思路的共同落脚点是民主。考虑到我国政经的现实体制,可以说,前一个方向的民主化充分考虑了现实利益和可行性,具有温和而保守的渐进色彩。而后一个方向,则具有激进的民主内涵,因为它是对直接民主的一种接近。
我国当下的这两条政改思路,一条温和,一条激进,并列地存在。但是,尽管两者同是在促进民主化的方向上走出的重大探索,看似是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实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取得党员身份是一个特殊的组织考察过程,而不像政府领导职位的选任那样是经过民主代表机关选举产生的(当然,这个说法征诸现实,不免太傻太天真)。入党的情形与参与一个社团一样,它以参与者的自愿和符合本团体各项要求的形式进行,而且其中的关键还在于符合条件、得到组织的同意。即使参与者各项条件都符合,够得上该团体成员身份要求的优秀层次,组织若不同意,参与者也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要求强制加入。公众参与式的民主化则是公民身份的直接兑现,当然不需要事先征求某特殊团体的同意。当这两个不同的民主化方向越走越深入的时候,党内民主将逐渐表现为特权者的少数人民主,而公众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将越发感受自己权力不够大、不够多。于是,两个本来按照预想,应该分别适用于不同事务领域的民主化方向——例如前者适用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领域,后者适用于政府财政预算领域(分别参见关于山西省县级党委常委会任免干部实行秘密票决制,以及浙江温岭公众参与县级参政预算听证的报道:http://news.sohu.com/20100516/n272148091.shtml;http://news.sohu.com/20100516/n272143156.shtml)——将会形成紧张甚至竞争和对立:前者越是采用更多的民主化措施,后者就越是需要在更多的领域、问题上参与,不然党员的特权与普通公民的无权就会对立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执政者为了疏导这种对立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会主动在自我改革的过程中,吸纳更多的公众参与。但也不排除另一种更具根本意义的方式:或许这种对立和竞争将演变成这样一种权利运动,即:获得党员身份的机会将被改造成一种类似于公务员资格的获取程序,它向所有适格公民开放,通过客观化的程序(例如当下的公务员考试这样的程序)来公平地竞争;又或者这种竞争采取更符合政治色彩的形式,将党员身份的获取改造成类似人民代表选举的程序。
从上述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下的政改,可以得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论。批评人士认为,我们的政改步子太小,搞搞形式,没有真实的内涵;当局者则认为,我们的改革将进一步巩固现有制度,但同时将祛除弊病、增进公正和效率。这里的看法是,两方面都错了。目前的政改虽是小步子,却可能导致重大后果;虽看似巩固现状,却其实不能排除形成宪政体制根本改革的效果。
现实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显露出上述逻辑结论的程度,而且可以肯定,人们也不会认真地认为,两个方向的改革会超出“必要的限度”,因为人们现在已经普遍地有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他们感到,公权力的这些姿态大概也就是一些姿态而已,不可能有实质内容。不过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两个方向自己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因素,因而的确也是不可能落实,或者不可能有实质效果的。就党内的民主而言,由于不存在与其竞争的第二个党派,所以,党内民主的最终结果只是取消它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的所有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永久执政的政党组织,假如实现了民主化,它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机关,例如一个议院之类的机构。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永久执政的政党之所以保持为一个党,是因为它内部的非民主因素,也就是通过组织从上到下控制人事等决定性资源;一旦它消除了这个精英式的机制,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反倒成了一个国家机构了。党内的民主化,只可能在两党或多党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性。出于这种内在的矛盾性质,我的基本判断是,改革的这条保守而稳健的道路虽然很好,但从主事者自己的角度看,却不可能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群众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更是不可能成为日常政治的主流。在我们这样人口庞大、事务繁多、技术复杂的社会,公民直接参与的可能性不得不限定在有限的地域或领域。从这个角度上说,应该很容易判断,所谓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化,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些“润滑剂”,而不是“钢结构”。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认为这里提到的两条政改思路都是歧路。这里还想指出另外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虽说政改的上述两种思路有冲突,但它们在当下却有共同的效果:它们仿佛一把剪刀的两片刃,共同裁减掉了人民代议机构。不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直接的公众参与式民主,都在跨过人民代议机构这个宪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似乎这个机构是可有可无的。监督法虽然表现了人大监督政府的重要地位,但却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旨在提高人大机构本身的议政和代表功能。在上面提到的温岭参与式民主中,普通民众与人大代表似乎同时获得了预算监督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权利。然而,我们知道,预算决算问题本属人大这个代表机关审查和批准的事项范围。现在,正当的法律渠道荒废不用,重新再通过政府自身的“礼贤下士”来建构民主途径,这本来就是对宪法的讽刺;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与人大代表出现在同一场合、同一层次,以发挥相同的功能。这样一来,我们很难理解,人大在哪种意义上称得上是人民的代表。情况倒是说明:人大这条渠道与人民之间根本就是缺乏链接点的。公众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化,本质上是在废弃代议机构的必要性。
从另一头说也是一样。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表现了代议机构的不必要性,或者说明了它的必要性之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两头加在一起,对代议机构构成的内外夹击。所以,从人大这个代议机构的角度和立场说,政改的两条思路,更难免有歧路的嫌疑。
那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是否有可能避免对人大系统造成结构性的损害?首先应当明确一点:我们不能为了保持人大代议机构的地位,就设想去压制既有的两条路子:假如没有党内的民主,或许人大将更出于不利地位;假如没有参与式的民主,人大将更少发挥功能的机会。因此,现实的出发点应该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化解党内民主、民众参与两者包含的破坏性成分,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方式,将这两个民主化的方向与人大代议机构关联起来,而不是将它架空。
但是,这项任务是极其困难的。只要党与人大是两个系统,而党同时又必须保持对人大的领导,那么不论是否实现党内民主,人大的位置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在实现党内民主的条件下,人大将更加处于无权和无意义的地位,因为党内一旦民主实现了,的确也就不用再把人大这个民主机关放在心上了——在党的民主的领导下,人大越没有独立性,也就是越符合民主。因此,现实的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让人大被党正式收编,从而将其转变为一个同时是国家的又是执政党的议事、决事机构。这样一来,党内民主化的措施就可以转化为对这个议事、决事机构成员资格的竞争。当然,除这种极端现实主义的方法外,人们还可以去设想其他理想主义的美好设想,但这里对这些幻想不感兴趣。至于公民直接参与这个方面,说起来似乎颇为简单,就是我们不要单单只注意行政系统吸纳公民参与这一个方面,而且还应该去设想一下,将这种直接参与的措施引入到代议机构的程序之中,将它们改造成实现代表与选民之间沟通的手段。这样,在代表个人与选民接触的非正式渠道之外,又将多出一条正式的制度化的接触渠道。
当然上述建议听起来充满了反讽:你这不还是等于把人大给废了吗?或者反过来说一样说得通:这是不是等于前面说的,执政党变成了国家机关?都是,又都不是。对此,实属无可奈何,只能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