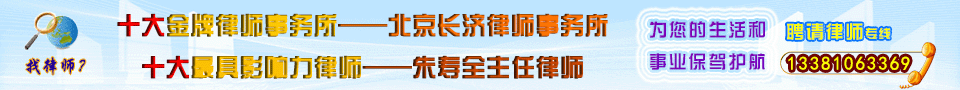南平惨案杀人犯的逻辑
《在线律师》网特约撰稿人 杜蘅
福建南平惨案的元凶二审仍被维持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但是这个杀人狂死不悔改,终不认罪,坚持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应该同时追究另一位案外第三人,因为他认定这位女士散布了对他不利的言论,企图陷害他。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一审、二审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这位被告都不曾流露出对被害人家属的歉意。
从法律人的角度看,这名罪犯有双重的认知障碍。第一重障碍用法律语言似乎很容易指明,那就是他无法分别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作为自然和生活事实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般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不是间接的因果关系;法律人的思考方式要求我们在无始无终普遍联系的因果之链上划出一个分界点,一端表示责任的范围,另一端则在人能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外。我们假设他臆想的事实成立,即第三人散布了对他不利的消息,企图“陷害”他,并且假设他杀人的动机的确与此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对于其故意杀人行为刑事责任的成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法律不允许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在法律人看来,指出这一点,实在是轻而易举。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以人的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即它假设一个人有能力在给定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其行为,并愿意承认此行为带来的后果归之于他本人。尽管这一点存在许多的例外,并且随着现代归责原则的多元化而逐渐变得模糊,但它仍然是刑事法律世界中的基础假设。这种能自由作出决定并承担责任的形象被称为“个人”或者“自我”。它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生活世界的一个规范建构。从这个角来看,对第一重认知障碍的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道德的认知问题上缺乏自我的观念。在这种思维看来,一切都处在普遍联系当中,单个的行为既是因,也是果;“我”只是之前许许多多前因的一个后果而已。
但是,我们注意到,本案被告人始终不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有任何的歉疚之情。这个情节是这个案件中除其杀人手段、杀人对象之外,最为令人震惊的一点。的确,他请求法院判处他死缓,这表示他愿意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重点在哪里?无疑,只在他对案外第三人的关系上。说到底,重点只是围绕着他自己这个中心的人、事、物,被害学生及其亲属则完全不在这个中心划定的范围之内,就好像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物件”,他的责任只是破坏了一些“物件”而已。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叫作极端的“自我中心”。与第一重障碍的思维方式相反,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不是打破界限作无限制地因果联系,而是划定界限:这个界限就在“我”,一个小小的躯体之内的“我”;我的重要性无限之高,“非我”的重要性则无限之低,甚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于是整个世界本质上也就是只剩“我”而已。整个世界只有“我”所看见的小小范围,除此之外全无意义。因此,法庭上的被告人总是对他自己的“被陷害”喋喋不休,而被害家属的悲凉和痛苦,一点也不能进入他的肉眼和心眼,就像有一道坚固而密不透风的城墙,将他的“我”密闭着一样。与第一重道德上的缺乏自我相对应,这第二重认知障碍,不妨被称为利害关系上的自我中心。这里的“利害关系”表示一个人注意力集中关注的东西。
这就是南平杀人犯的逻辑:在责任上,他采取普遍联系的观点而“考虑”他人,从而将责任推脱给他人,结果是产生出不负责任的无能的人(负不了全责,因为他的行为是某个前因产生的后果);在利害关系上,他采取相反的观点而忽略他人,从而将利害关系集中到自己,结果是产生出无节制的冷漠的人(无节制地关注自我就是冷漠)。面对这个冷漠的杀人犯,我们一定都感到他让人无法理解的异类性质,一定都感到他是一个不幸的特例,是正常生活中一个突然降临的灾难,就如一场地震一般。然而不幸的是,他并非像表面上给人的感觉那样是一个例外;相反,这一杀人犯的逻辑已然是弥漫整个社会的逻辑。我们的制度实际上要求的就是道德上无能的人,而这种道德上无能的人,扎根在一个普遍联系的权力网络中。这个权力网络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例如,法官的责任溶解到合议庭,合议庭的责任溶解到审委会,审委会的责任溶解到法院,法院的责任溶解到政府,政府的责任溶解到党组织,党组织的责任溶解到上一级……如此逐级往上,似乎最终,一切责任都只在这个链条的结尾处——在那里大概存在一个“第一因”或“第一推动力”。在这条普遍联系的锁链中,没有所谓的权力部门间的界限;它们通过“权”这个通货彼此可以通约,其中的差别只是数量多少(权力大小)。如果没有上头的意思,似乎谁都不能在这条链条中突出出来承担责任。辽宁省庄河市市长面对集体上访下跪的局面逃之夭夭,简直是对我们这一判断最生动最形象的说明:似乎该当家该做主该担负起责任的人,关键时刻掉链子,逃走了。最近,北京市发布公选数百名副局级以下公务员消息,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似乎这当中体现出了人才竞争、择优上岗的良好理念;殊不知,这只不过是公务员群体自我特殊化的一次操作。实际上,在充分的法律与相关文件的支持下,公务员队伍逐渐在形成一种基于权力的群体身份认同,而面向社会(实际上还是面向公务员群体)的公选,实际上打破了常规的权力等级体系,打乱了常规的升迁过程,让人见识到“上头”的权力可以穿越任何屏障。而“上头”的权力之所以可以这样畅通无阻,就是因为所有的界限,包括权力内部的界限,对于权力本身来说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这里,一个掌握权力的环节因为对他的权力没有界限,所以他的权力看起来可以是无限大的;但要说承担政治的、道德的责任能力,却是无限小的,一定要往上归结,因为恰恰因为没有界限,“上头”只要一说话,它就必须听命了。
官员群体内部这种权力上下左右的畅通无阻、冲破界限,教化并带坏了整个社会。我们常说我们的社会是个关系社会。这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权力社会。权力打破了整个社会的一切界限,社会上的权力与官员手中的权力、钱与权、色与权、情与权等等等等,这些本来在不同领域的东西,现在也能够互相换算。这真正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我们的优秀人才就是在这种所有领域“水乳交融”的环境下培养出来并被输往最高最贵的权力系统的,输入到一个想负责而不能的体制之中,最终他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无能者。
但是,这套权力机器的逻辑还有另一面,和南平杀人犯的想法是一样的。一旦出现“事故”,牵涉权力自己的厉害关系,它就不再把自己这个系统看做彼此联系的,原先被打破的界限突然出现了,并且还要生生地制造区别,例如正职总是善的、好的,副职在必要的时候要被忽略,出的问题总是他们负担;书记总是善的、好的,市长则总是要倒霉,关键的时候要被忽略,不再计入他对整个联系网络的“贡献”;上级总是善的、好的,下级在必要的时候就必须被忽略,不再计入它对整个上下系统的“贡献”;中央总是善的、好的,地方往往不像话,要枉法,问题一出肯定是地方的,绝不会是中央的。如此等等。这和南平惨案元凶的想法有什么区别呢?他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冷漠,表示被害人及其家属被排除出了他的世界、他的考虑,而权力系统中这种“清理门户”的作为,难道不也是在把这些所谓的具体的“责任人”排除出权力体制自我纯净化的世界吗?实际上,假如权力系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链条,责任就应该一直往上归结;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出现了具体的责任人,那么权力系统就不是一条没有界限没有法度的链条——与此相应,假如南平杀人犯要考虑第三人的前因,那他要是一以贯之地对待,就应当也考虑他的后果;如果他不把后果计入考虑范围,那他也无权要求法庭考虑他的那些无关的前因。
呜呼!原来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相矛盾的“杀人犯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