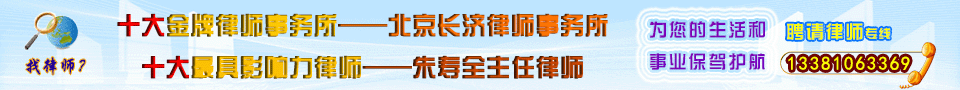官僚的统治
——谈因上访被判敲诈勒索罪的象征意义
《在线律师》网特约撰稿人
杜蘅
诸位看官,如果你不喜欢过于理论化的说法,那么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希望你耐心看完这些略显枯燥的文字,你会发现,我原来是想向你说明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上访者会被判敲诈勒索罪。你知道,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已经不止一件了,山东、山西等地,已经发生了多起。
我在上一篇文章《上访、控访与民主》中说,上访问题本质上是个民主问题;它之所以反复成为政府治理中的难题,是因为我们的官僚系统本身就不能作为民主责任的载体。这个官僚系统的人员在来源或选任上、在行为方式上,以及在责任方式上都不是民主的。从人员选任方面讲,这个体系一直在两个方向上进展:一个方向是组织系统的考察、委派,它的本质是上级培养、考察和任命下级,而不是从下往上的民主选举;另一方向是资格能力考试,就是目前千千万万人挤破脑袋的公务员考试,包括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考试——这种方式注重的是专业能力(考试报名资格往往限定了一定的学历及专业方向)。这两个方向,再加上公务员身份在制度上的特殊保障(薪酬、保险、福利、退休、医疗等等),塑造出的官员行为方式主要是向上级负责,以及职业化心态——实际上这种心态更多表现为特殊阶层的权贵意识;而这个群体相应的责任形式是无责任、推脱责任、转嫁责任。这一点我在另一篇文章《南平惨案杀人犯的逻辑》中也作了描述——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官员是无能的。
不过,这种官僚化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发现它的蔓延。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这种趋势概括在“世界的理性化”这个名目之下,认为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发展兴盛共同构成现代国家的特征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官僚化是在疆域辽阔、问题复杂的大国之内,为了达到行政上的高效率而不可避免的技术手段——尽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高度发达的官僚系统是否真正取得了高效率行政的效果,这一点还是值得怀疑。韦伯提醒人们注意,官僚统治是没有能力对民族真正负责的,因为——往好里说,如果他们真正体现出他们独有的精神特质,那么他们的秉性将是服从上级;往坏里说,如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升迁,那么他们的倾向将只是成为油滑的追名逐利者。无论是表现出好的方面,还是表现出恶劣的方面,他们都不是对人民负责。为了对这套行政系统进行控制,就必须有一个不同的政治机构,例如足够强大的议会系统,来掌握领导岗位的分配权力。议会的行事逻辑与行政官员不同,他们作为选出的代表,必须通过竞争争夺民意资源,因此,他们倾向于向人民负责,并且也因此,政府系统的领导岗位在向议会负责的过程中,间接受制于公众的压力。
我国的制度安排在表面上与韦伯的设想颇相符合,似乎我们的立宪者完全理解了其中的道理。不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宪法都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位。从形式上看,行政机关,或者也包括司法机关,将因此而间接地向当地的人民承担起政治责任,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去约束本行政系统内部的所有事务型的公务员。但是,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些想象中应该发挥作用的逻辑一概都是纸上谈兵,一概都归于无效。用我们在法学中经常听到的说法就是,行政系统独大——实际上是行政系统吸纳了那个本应当向之负责的代表大会,吸纳了本应当与它并列的司法系统。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里有的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官僚的统治。
不要以为,这是具体执行过程中法律规定走了样,或者认为这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歪曲造成的结果。相反,这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刻意安排的。例如,虽然省、市、县、乡、镇的政府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它们的行政上级实际上权力比它们大,它们是要听上级的(用法律条文说,比如: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通过这条行政系统的上下级负责的线索,宪法建立起来的行政向人大负责的要求,一下子就被从下面到上面打穿了,一直到中央的层面。那么你说,你怎么让官僚向人民负责?——暂且不去说什么代表选举的自由度问题了。
之所以官僚逻辑能够吸纳其他本来与它本性不同的领域,最为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里。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学术研究机构、高校、司法系统有过多过滥的行政化。为什么?答案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说:行政化太多了,要减少,要控制,要抵制,要排除。这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看到,人大、行政、司法,这三个系统本身的建立方式是不同的:人大是下面选上面,行政(除了人大选举的领导职位外)是本系统内的上级任命下级(以及底层的考试进入),司法系统的人员选任在我国确实与行政类似,但它至少在法律层面与行政是独立的。但是这三个不同的系统却被行政统一起来,这其中只说明了一点:有一个更高的第三方在左右局面,而这个第三方自己的组织逻辑、行为方式、责任方式,都与行政系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唯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最终是行政系统超过了其他系统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更高的第三方,即执政党。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被官僚化—理性化的现代趋势俘获,它不得不也成为一个官僚治理的系统。
说了这么多,最后该回到我们的正题了:为什么因为正当理由上访的上访者,竟然会拿到一纸判决,说他“敲诈勒索”政府,罪名成立?(相关报道见:http://news.qq.com/a/20100506/000212.htm)在这里,我不打算去争议这样的司法判决在法律论证上是否站得住脚——因为它实在太站不住脚了,不然《信访条例》岂不成了“违反刑法”的行政法规?(参见《海南日报》的报刊文章:《群众上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07/2268912.shtml)。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批评当地司法机关太过缺乏独立性——这种过分超出常理的荒谬判决,最自然地说明了司法系统受制于行政系统的事实。我想指出的是,这个判决是官僚统治明目张胆的自我表白、自我宣告。上访者请求行政系统出来承担责任,他的意思当然是政府与他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应当向其支付应当支付的款项、赔偿应当向其赔偿的损失,即使就具体案件而言并不存在这种给付或赔偿的权利义务问题,政府也仍然存在一项公法上的义务,根据法定程序和权限予以调处、驳回或作出其他决定。但是政府系统却罗织出敲诈勒索的罪名,这意思就是说:我政府和你公民之间并无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相反,我们两方的关系只是彼此没有任何特定法律关系的财产所有者和一个偶然觊觎我的财产的路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设想政府与上访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到,政府可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呢?在真正出现政府被敲诈勒索的情形中,敲诈勒索一方——例如暴力的恐怖分子、走私贩毒分子等等——事先就已经把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两个彼此并无法律上责任关系的对立主体了。在我们的案件中,情况相反,不是那个“敲诈勒索”的上访者,而是政府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定位,这岂不是官僚系统固有逻辑的自我宣告?
在这个入罪的判决中,以政府为一方,以合法行使权力的公民为另一方,形成了赤裸裸的对立。这种对立比骚乱中的群众拿起武器与政府对立还要极端和激烈:拿起武器的对立说明两者形成了敌对关系,群众一方还有拼死一搏的独立性;而在我们所说的案件的对立中,上访人却缺乏这种独立的地位,他完全处在一种无比委屈的不利状态,因为他的对立地位不是他意图的结果,而是被制度的复杂性诱骗的结果。官僚统治的基本逻辑不是向人民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是向本系统的人事任命权限系统负责。因此,上访者要求政府来向他的损害状态负责,自然的倾向是要求上级来对他负责;但是既然下级官员自己也是是向上级负责,于是这里的下级官员便直接与上访者构成了竞争关系。在这对竞争关系中,我们本来可以指望官员的上级有可能不偏袒任何一方而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进行处理,但是不巧,我们的这些上级与他们的下级实际上处在类似的地位,他们也会遇到上访者要求这些上级的上级来负责。因此,这些上级感同身受,他们的动机就被塑造成“官官相护”。于是上级打个批示、写个纸条,把案件重新交给那个本应承担责任的下级去处理,最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结果是,整个政府—行政系统都和上访者处在对立中,但那个叫《信访条例》的文件却郑重其事地告诉上访人,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信访途径主张权利、反映问题、表达意见、检举揭发。在它的引诱下,上访人一不小心就走上了与政府对立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遮遮掩掩,以请住宾馆、党校及其他威逼利诱的“不太”违法的手段对付他们;现在,敲诈勒索罪的判决终于堂而皇之地大声宣布:上访者与政府处在对立关系中,这种对立就如财产所有者与敲诈勒索者之间对立一样。这无异于宣布:政府系统与人民处在对立之中。在两者之间发挥调和及控制作用的那个真正负责任的人或者机关到哪里去了?
再重申一遍:政府或者行政系统自身固有的逻辑是向上级负责,是固守具体的事务,不是承担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因此它虽然与人民在日常行政中直接接触,但却并无直接的责任关系。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外在的、间接的关系。人民竟然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它来直接向他负责,从而扰乱它自顾自的逻辑,搅扰它的清梦,它岂不是要告你敲诈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