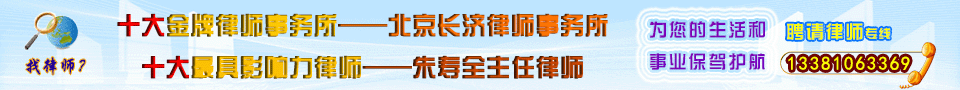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社会百态〗
据新华社电,世界贸易组织27日正式任命中国律师张月姣为该组织的上诉机构成员,这是中国内地的律师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是该组织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除张月姣外,来自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其他3名资深律师也在当天的会议上被任命为上诉机构新成员。他们将分别接替即将退休的4名现任成员。
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要求,上诉机构成员必须是公认的法律、国际贸易以及世贸组织协议方面的权威专家。候选人由世贸组织成员提名,须经过由世贸组织总干事、总理事会主席、争端解决机构主席等高官组成的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和推荐,并由争端解决机构在全体成员会议上任命之后才能任职。
根据世贸组织提供的资料,张月姣现年63岁,曾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为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等职务,并担任过中国知识产权谈判代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法律顾问,现为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月姣在上诉机构中的四年任期将于明年6月1日开始。〖聚焦〗
从中国律师张月姣被任命为世贸组织法官一事,自然会联想到我国法官制度中的一些现象并产生疑问:张月娇能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作法官,类似这样的律师在国内有机会当上大法官吗?为什么我们国内很少有律师被任命为法官,是国内法官职业的从业门槛高,还是法官职业的吸引力有限?怎么看待国内一些法官辞职作律师,是法院的行政化作风,还是薪水不高?但愿本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此,只谈我国的法官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国内审判机关行政化体制弱化了法官中立性、独立性。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个至上的条款被解读为“人民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法官的个人独立。”这在我国都快成老生常谈了,有数不清论文著述。
审判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核心,法官是中立的裁判人员,是正义的化身。行政与司法在我国分立已100来年,而现实中政府却仍然常常把法院视为自己的一个职能部门,让司法机关承担行政职能。前段时间,某地方政府为了争创文明卫生城市, 应付上级检查,居然要求法官集体上街去捡烟头、果皮。人、财、物都被行政部门控制的司法系统,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我的地盘我做主”。在社会生活上控制了某人,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某人的思维。从西方引进的司法制度,本来是为制约行政权力而设,有完备的程序制度设计,在我国却染上了浓厚的行政官僚主义习气。法官被分成十二等级,法官与法官之间名义上是监督关系,实际上却是领导关系。正是因为法官有了党委、行政等如此多的上级,其个人独立便无从谈起。判案的实体权利由既不参加庭审又不署名的领导行使,法官、甚至合议庭都只有过堂、署名等一些程序上的权利。行政官僚作风对司法领域的不当干预过多,使法官独立性缺失,使审判效率打了折扣。一味强调法院人手不够是没有理由的。我国的现任法官人数居世界第一,但每位法官每年审结案件数还不到美国、泰国法官的1/40甚至1/100。 凯普利堤认为:“司法独立本身并不具有终极价值;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只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审理案件。”
第二,国内法官职业权威性不高。
想起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说的一句话:“我相信法律,但怀疑法官。”在欧美等法治国家,当事人输了官司可能怀疑律师,但决不会去怀疑法官。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会象对教堂的神父一样尊崇法官,法官就是人化了的公平正义,法官就是正义之神。职业的神圣化,才能彰显裁判的严肃性、中立性及权威性。而在国内,法官经常被怀疑是“是吃了原告又吃被告的人”。零点调查公司曾作过调查,法官的可信度在我国的所有行业中排名靠后,而欧美日等国的法官却排在第一位。权威性不高,待遇也不高,当然难以对律师产生吸引力。《中国律师》前主编刘桂明在博客上写道:“如果说,我们的‘司法权威’已经病得不轻,那我们的药方在哪里?如果说,我们的‘司法权威’已经病入膏肓,那我们的司法体制还有救吗?”也许我们得齐心协力、集思广益为它寻求一剂猛药。第三,法官职业大众化顽症未除。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在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的司法领域有三大顽症,即“法官职业大众化,审判过程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
1995年的《法官法》对法官的任职要求不高,许多退伍转业军人、政府工作部门的人员甚至事业单位的人员都进到法官队伍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学习,稍微培训一下就开庭审案,学历不够的就到党校进修混拿文凭。老一代法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2001年的《法官法》修正案,对法官有了学历要求与通过司法考试这两个较为硬性的条件。但在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这又使两个条件在法院的领导职务上有特殊。本来我国审判人员的独立问题还未解决,让一些“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进到了审判队伍中来,来了还是当领导。因此,在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情况下,“没参加庭审的人却是作出判决决定的人”的情况也就不是很少见了。
在法官选任把关松懈的背景下,大众化的法官职业却从来没有对律师大众化过,这也许是法官任用制度模式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取“律师资历前置”模式,而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司法考试加法曹培训”模式。两种不同的法官选任路径,体现出很相似的要求:不仅要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素养,还要具备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国内现在的《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任职最低年龄是23周岁,年纪轻轻就能当法官。法官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积累,难以胜任“正义之裁”的神圣职务。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在于经验。”波斯纳也有过类似的名言,法官并不需要天资绝顶,但必须通晓人情世故。在过去由于法院的工作压力,对法官的选用把关上稍松可以理解。但如今还依然重复着过去的故事就说不通了。第四,法官职权范围的限定问题。
哲人语:“法官的职责在于裁判,而不是发现。”在西方当事人主义(或者称对抗主义)模式下,法官消极中立,不主动调查案件,把事实问题交给陪审团决定,然后由法官根据陪审团的决定依据法律作出裁判,是近乎于人类理性的。官与民,本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却变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英语中的judge(gentlemen
of the long robe),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居然也被翻译成了法“官”。相类似的还有,本不是一级政府的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上是“基层自治组织”,却还有“大学生村官”的叫法。 所以在现有体制下,法官还做行政事务。有的地方政府,居然还要求法院承担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行政职能,到京城劝返上访的百姓。同时,行政机关本是法律执行机关,却演起了“法官”的角色来,有时自己甚至还一边踢球,一边吹哨。更绝的是,让法官在许多问题上无法裁判,或者不能裁判。因此,法院要去履行本属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本属自己的职权范围的事又被行政机关给“代为行使“了。彻底厘清行政与司法的职权范围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必须,也是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第五,加强法官法律思维训练问题。
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法律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传统,它不是生活知识的大杂烩,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就无法胜任“社会医生”的职责。况且良莠杂处的结果往往是“劣币逐良币”,残次品充斥市场。只有统一的法律训练,才能消除鱼龙混杂的局面,使他们获得法律思维的头脑。作为法律职业中最权威的的核心的法官尤其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