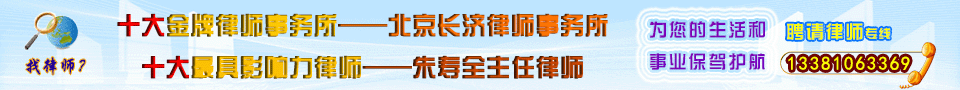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 首页>>律师成长之路>>知名律师纪实
 律师成长之路 律师成长之路
《在线律师》汇编
知名律师纪实 系列文章
王俊峰:中国最大律师事务所掌门人
国际航空报
http://www.66law.cn/archive/news/2008-02-25/21633_1.aspx
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这么多年,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看到他们就刺激他们、打压他们,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中国律师可能平均一个合伙人收外国客户四五百美元一小时,但外国律师提供的服务未必比我们更有效,他的收费可能就是一千、八百美金一小时,这对市场的侵略和影响还是挺大的。
在美国创立首个中国律师事务所
本报记者:1999年,你在美国硅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现在回想一下,这对于你个人和中国律师行业意味着什么?
王俊峰:当时在硅谷设立分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有个窗口,能更多地了解学习,能非常深刻地观察。在美国硅谷,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也有中国公司要到那里投资,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法律市场环境。我们希望我们是个窗口、是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能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我觉得是个尝试,是最初始的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本报记者:在硅谷设立律师事务所后,当时美国当地有什么反响?
王俊峰:那个时候,中国律师行业在国际律师行业里还很弱。美国对我们在硅谷设立中国律师事务所,基本的态度是积极、关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国内、亚洲法律服务行业有点压力,中国律师象中国企业一样早晚有一天会走出去。
本报记者:你们现在在美国有自己的分所,与美国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相比,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王俊峰:作为窗口、桥梁,我们的律师事务所重点是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在做些市场开拓,让当地的美国人了解中国,还构不成对当地律师事务所的直接竞争、直接威胁。当然,通过窗口,我们可以学习。与2000年相比,我们现在有了很大进步,逐渐建立、形成了很好的客户基础,建立了很多的业务网络。我们也设立了纽约分所,我们是唯一的在美国东岸、西岸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本报记者:你们的律师事务所创建立14年来,你所感觉到的国家在法律建设方面的变化和公民的法制观念、对法律的依赖程度的变化是什么?
王俊峰:这方面感触较深,用一句话概括,感觉法制建设、变化特别快。首先,从立法角度,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很少。到现在,从全国人大到地方人大特别是最近两年,立法脚步又加快,而且向比较深层次发展。近两年,有好几个新的法律颁布实施,比如《企业破产法》、《反垄断》、《物权法》、《劳动合同法》。法制是和民主、人权密不可分的。比如物权法,直接涉及了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我们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国外来看,就象空气和水一样那么普通的观念。而在我们国家却经历了几十年。但它一旦确立下来了,对国家发展、进步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老百姓也有着深层影响。
比如,楼房以前说用50年或70年就没了,那老百姓就没安全感了,对开发商也一样有影响。这个楼既然只用70年,那开发商盖这个楼,在质量上也就不考虑百年大计了等等。另外,这种法律唤醒了或者说加强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比如说,物权法公布后,老百姓打官司的多了,老百姓法律意识提高了;劳动法施行后,更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权,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雇劳动者了。这些基础性的、框架式的法制基石性方面的进步标志着我们国家新时代的开始,这对加强老百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独立的公民意识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确确实实加强了社会和老百姓对法制的依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如果律师业被外资控制
本报记者:前段时间,外资的法律服务机构开始进入中国,开始拿走涉及商业机密、技术机密的案子,你认为中国的律师行业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
王俊峰:我觉得整个国家、行业普遍地对这个问题觉醒和意识不够。法律服务表面看是社会服务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法律通过企业窗口渗透得很厉害。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会计师行业。十几年来,国际会计师巨头占领了国内80%以上会计、审计行业的高端领域,把本土会计师打得落花流水,中国的会计师依附在他们身上在下游工作。中国不像一般的小国家,小国家的国际影响不大。但中国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东西方的平衡是有巨大意义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国家的软服务领域应该有高度的意识,对发展要有前瞻性。
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完全放开外资法律服务机构在国内的法律服务。有的外国律师事务所甚至是非法执业的,做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做的事情。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国家对外国法律服务机构监管、限制不够;二是深层次地反映出我们国内律师事务所发展水平比较低。由于绝大多数中国律师事务所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法律服务产品比较单一,外国律师事务所就来大行其道了。如果现在对他们不加限制的话,国内的律师事务所就会一直无法抬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还要开放,看到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国际经济、社会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有意识进一步发展我们自身。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现在的法律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高科技领域。国内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的产品基本上在中下端,高端的服务产品都被国外律师事务所把控。我觉得,整个行业、国家及主管部门一定要对这个局面有很好的、清醒认识,并应有所应对。
本报记者:你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有所应对吗?
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自创立那天起,就注重从国际市场上吸纳精英。我们的法律服务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直接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在竞争。但现在单单在中国市场上可以承担一定份额和使命已经不够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也是必然趋势。中国律师不仅要在本土法律服务领域担当主角,也有责任有义务跟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说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样的使命面前,中国律师行业就显得比较弱,绝大多数外国律师已经把市场瓜分得差不多了,并把目光瞄向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我们压力还很大。坦率地讲,金杜还是很自信的,我们生长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和成就。但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国家,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整个国家、整个行业有这样的关注,才能引导、调动和组织整个行业来尽快应对,才能在未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或承担这样的使命。
本报记者:你们和国际大的律师事务所相比,还有什么样的差距?
王俊峰:作为本土律师,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有更深的理解,我们提供的法律产品、法律服务可能更有效、更有意义,但和百年老店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中国律师可能平均一个合伙人收外国客户四五百美元一小时,但外国律师提供的服务未必比我们更有效,他的收费可能就是一千、八百美金一小时,这对市场的侵略和影响还是挺大的。坦率地讲,我们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同行间的交流和促动。
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本报记者:针对国内的法制环境,不少律师比较失望,甚至想放弃律师这个行业,你怎么评价当下的法制环境。
王俊峰:如果有这种想法,要不是他比较片面,要不就是他态度不够积极、不够进取。我们的法制环境还是在不断进步的,逐渐被国际接纳、认可和肯定,如果看不到这点,那完全是个人片面的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法制环境在现代的国际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需要改进、升级。法制要和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法制环境有它特殊的方面,但也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完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制水平可能和人们心里的法制理想还有一定距离。如果说到具体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有社会下的所谓的不公平。从积极方面看,我们国家政府很关注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环境还是在朝积极的方面发展,这是要肯定的。
本报记者:在一些地方,“公检法”的形象在一些老百姓心目中比较差,作为律师行业从业者,你怎么看?
王俊峰: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国家社会很稳定,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和我们国家的公安、司法体系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个主流是要肯定的。至于说极端的案件,需要我们去改善减少。美国也有,但确实不该回避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完善我们国家的司法体系、推动司法改革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一种文化、一种体系的建立,不能简单化,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夜就能改变的,它有渐进的方面。比较好的是,所有人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十七大报告中讲到,改革、发展是主旋律。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就没办法谈改革、谈发展。在稳定的环境上,谈发展、谈改革是理性的、是循序渐进的。
我没有乌托帮式的理想
本报记者:你小时候喜爱文学、艺术,现在从事法律工作,这种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对你从业有冲突吗?
王俊峰:我觉得没有冲突,反而对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小的时候,喜欢看小说、唱歌跳舞;上大学时,也梦想着去部队、政府部门、做外交家,确实没想过当律师。毕业分到贸促会,有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看到了法律对于国家、社会、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法律环境、法律职业这方面的空缺还很多,特别是跟国际律师同行相比,差距还很大。
我经常跟媒体讲,那时对我刺激最大的是,看到有的中国人在外面读两年书,被外国律师事务所聘用了,回来后那种自豪感让你很刺激。那时候选择出来做律师,就是希望改变一些现象。当时我在贸促会工作,要想在体制内干有些事是不行的,会受体制内很多方面的限制。于是就走出体制来到了市场。这么多年,我们经常看到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看到他们就刺激他们、打压他们,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一回来,我们都很尊敬他们。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律师工作,没办法停下来。越做法律工作,就越不是兴趣了,而是种责任。特别象以我为主创立了律师事务所,我的企业文化、创业精神召唤了很多人。大家作为合伙人,就有责任共同面对很多问题。文学艺术的爱好使你对人性有很多的了解,让你懂得去尊重别人的劳动,这方面很重要。一个人不管你做什么,其实就是两件事,就是为人和做事情。为人往往比做事情更重要,为人就是要诚实、懂得尊重别人。如果你有了这个基本理念,你做起事情来就会容易,而且你会尊重团队。我们经常是做商务律师、金融律师,需要深刻理解委托人的需求、他的发展、他的真正利益在哪里,然后帮助他实现。这里面有很多艺术,需要非常专业的灵活性。
本报记者:你每天都和不规范、不合法的事情打交道,这会影响个人的生活和情绪吗?
王俊峰:不会。我们接触的都是国际上一流的大公司,探讨的都是前沿的话题,但也会接触到一些不太阳光的东西。我走南闯北,经历比较特殊,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更多的还是理解。
本报记者:自己最满意的事和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
王俊峰:当我的女儿学习取得了好成绩、生活很健康,这会让我感到很满意;当我听到我的合伙人、律师得到了当事人的夸奖,我会很满意。至于我自己,好象没什么让我感到很满意的。
至于困难,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挑战。我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头,我没办法跟别人讲困难。我永远要鼓励大家、说希望。我们尽量不要惹事情,但我们不怕事情,遇到事情我们想办法去解决。但内心的压力和挑战每天都有,来自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本报记者:现在从事的事业是你理想的事业吗?
王俊峰:我从小喜欢文学、艺术,律师职业和我所有可以想到的理想都不搭界。但人生无常,我现在从事律师行业,我们这个集体是社会很小的一个细胞,但我在这里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时代的脚步。虽然我们的事业是小的,但我们跟着时代的进步,在帮助中国法制做贡献。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大的,这会感召我们往前走。
本报记者: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的规划或安排吗?
王俊峰:希望事务所早点能成熟起来,能建立起更稳定、成熟的运行机制,很健康、积极地发展,我可以有自己更多的空间。我最喜欢看书、写点东西,我每天都会看书,但我会尽量控制写作的冲动,有时也会在事务所内部发表一些感想。
本报记者:你比较欣赏的同行是什么类型的?
王俊峰:我们强调专业素质,法律人都有本的气质和素质,只要他有基本的素质和气质,很严谨、很诚实、很勤勉、有责任心,这就是好同行的形象。
本报记者:作为六十年代的人呢,你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王俊峰: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恐惧,除了责任、理想、做正确的事情之外,别的事情看得淡。
恐惧也不是我自己的,比较担心行业的进步、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我的理想是无论国家还是集体、行业都能不断地发展。我已步入中年,理想和现实比较接近,不会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有理想但会比较现实,会少些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