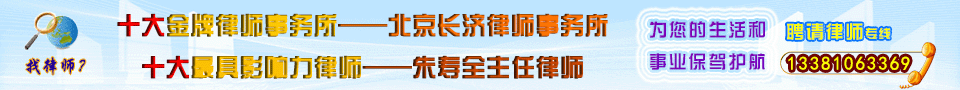法律人生的内与外——江庸先生侧忆
法制日报
近代中国的法律人,往往是忙得“不亦乐乎”的,因为他们担当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常常穿梭于不同的场域之间,而非仅仅坐审论辩于法庭之上、或沉思于方寸的书斋之中。创造历史的人们总是忙碌的!中国近代法律名人江庸,就是这样的一位“忙人”。
江庸(1878—1960),字翊云、翼云,号澹翁,祖籍福建长汀,生于四川壁山。其祖父江怀廷,咸丰年间进士,在四川等地为官,其父江翰,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文科学长和学部参事等职。江庸幼承家学,旧学功底深厚,1898年入成都中西学堂,1901年入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两年后,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1906年回国,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但未赴任即改由学部调普通司任职,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不久,修律大臣沈家本聘江庸为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法律学堂教习,1907年调任大理院详谳处推事。1909年江庸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获廷试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民国成立后,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不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1913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庸任次长。在政潮迭起的民初岁月中,江庸其后又数次出任司法次长、总长。1920年任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1923年,江庸辞去所有职务,在北京执行律师业务,并创办《法律评论》周刊,任社长。1924年受聘为国立法政大学校长,次年辞职。1927年起任朝阳大学校长,培养了大量法律人才。1935年华北危机日剧,江庸南迁上海,曾为“七君子”出庭辩护。抗战爆发后,江庸多次拒绝出任伪职,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去重庆,执行律师业务。1943年江庸被推选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执业律师。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宪法”,宣布江庸为大法官,江辞不就。
1949年初,受代总统李宗仁之邀,与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等人赴北平试探和谈之途径。是年秋,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江庸任国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馆长等职,1960年病逝于上海。
江庸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代,“感受”了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波谲诡秘,同样,他个体的生命史与近代中国的“大历史”纠缠在一起。作为一名法律人,江庸亲历了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历史进程。参与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或法律实务,或法理探究,或投身法律教育、或创办法律报刊,等等;角色不可谓不多:或为司法官、或为司法行政官、或为职业律师,或为参政员,不一而足。
江庸早年接受新(日)式法政教育,回国后即厕身法曹,法政探研与法律实务两不误。革命军兴,民国肇建,国体变更,代表新政权行使司法权的司法官重新任命,作为新式法政人员中的佼佼者,江庸自然能在新政权中继续留任,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次长、司法总长等要职。当然,江庸对中国近代法治贡献最大者,多半要数他创办了法律名校——朝阳大学,“无朝(阳)不成(法)院”,成为那个时代法界的流行语,“门生故旧”遍及海内外,他也因此被誉为法界耆宿、泰斗。作为一名法律人,江庸的人生无疑是丰富的、成功的。
如果说上述是江庸法律人生的“份内”之事,那么,他还从事许多“份外”的工作———诸多其他的社会角色,显著者有二: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江庸穿梭于不同场合之间,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名流,如梁启超、章士钊、颜惠庆等,过往甚密,并斡旋于不同派别之间,还曾一度为国共和谈劳心劳力。和江庸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儒雅”,具“魏晋名士”之遗风,彰显着一位文化人的角色存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在书店坊间或图书馆的古籍书库看到他遗传下来的许多游记、随笔、诗词,如《渡台日记》、《欧航琐记》、《趋庭随笔》和《澹荡阁诗集》、《攻错集》、《入蜀集》、《汗漫集》、《旋沪集》、《蜀游草》、《南游杂诗》、《生日游百花山诗》等诗文(诗文大部分已收入《江庸诗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所有这些均表达着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才情。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诸多角色的同时存在,使得江庸“精力不济”,例如,他在法学学术研究方面,能为后人所称道者并不多。其实,这是近代中国许多法学家的共性,如王宠惠、王世杰等,他们虽以著名法学家名世,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能传世的法学学术作品并不多。这不仅从他们忙碌的法律人生——多重的社会角色中求解,亦需明白,跌宕起伏的近代中国不是法学家“施展拳脚”的理想环境。此外别忘了,法学本身是一门讲求“实践”的学科,它不可能像文学、史学那样,成为一门“书斋浓度很高”的学问,更何况近代中国法学本质上是“舶来品”。故法学家没有多少“自己”的学术产品,实属正常,不可苛责之。
言及江庸,不可不提的是他的民族气节。日寇入侵,很多国人沦为民族罪人,而江庸则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硝烟弥漫长城内外、“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候,他在为朝阳大学毕业生同学录所作的序文中写道:“诸君,今岁毕业之时为何时乎?非外患日迫国家存亡莫卜之秋耶。然以吾国区域之广,民气之强,百足之虫犹死而不僵,抑岂区区三岛所能兼并!”表达了这位身兼法律人、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等诸多角色于一身的现代国民的民族情怀——乐观,又不失坚毅。这种民族气节和情怀,是江庸法律人生的“内”?还是“外”呢?我想,也许不可如此“截然两分”吧!“内”与“外”的结合,便是我们后来人看到的那个时代法律人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