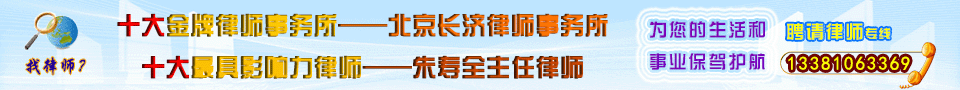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 首页>>律师成长之路>>知名律师纪实
 律师成长之路 律师成长之路
《在线律师》汇编
知名律师纪实 系列文章
田文昌律师的非法律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 文/李菁 田文昌所在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在北京朝外大街的一座价格不菲的写字楼上。作为被封为“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田文昌的这间办公室显得毫不张扬,除了一些法律专业书籍、照片和诸如“北京市十佳律师”之类的证书外,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着的那份由“美国国家刑事辩护律师协会”授予的会员证书。田的助理卢伟华说,得到“终身荣誉”会员资格的,中国只有田文昌一人。
6月底,田文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采访,其间一个讨论话题是对律师这一职业的定位。田文昌再次重复了他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只是通过参与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来实现和体现法律的公正。”节目中,田文昌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当事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即便主持人设置了一个难题——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前者是否仍是第一位——来发问,田文昌的眼神没有丝毫躲闪,“必须是这样,否则你就不是律师。当然前提是依法履行职责”。
“实际上,我在这个节目中说的一些话已经触了‘禁区’。”7月17日下午,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田文昌谈起那天的采访。田文昌的咽炎很重,不停咳嗽、清嗓子,却又不时掏出身上的中华烟点上一根。在西方,“律师的职业定位”已是无须再讨论的话题,但在眼下中国,“很悲哀的是,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田文昌用“困惑多、辛酸多、尴尬多”来形容自己。
3年前,河北农村的一个村支书被指控侵占,法庭设在县里一个大俱乐部里,不少“光膀子的、抱着孩子的”村民前来旁听。田文昌为村支书做的无罪辩护很成功,“可能是村支书的人缘是差了点”。休庭期间,许多村民围了上来,要打田文昌。法院赶紧找人把田文昌护送到后台。法官告诉田文昌,“不敢判无罪,因为无法向老百姓交待”。县法院的策略是给中院打电话,让中院改过来。“二审开庭后,检察官完全支持我一审辩护词的意见,表示他无罪;更奇怪的是,控、辩双方都认为无罪,没起诉方了。但中院仍不敢当庭宣判,拖了一年之后才宣判无罪。”
对律师商业性的质疑也是对律师职业的不了解。某年,一位40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来找田文昌咨询。咨询过后,谈到律师代理费用,那位男士突然表情一变,“你还收费?!”然后转身离开。“那种鄙夷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得。”田文昌说,要在外国,光是这么长时间的咨询就该论美元收费了,“我还没谈收咨询费呢!”
几年前的一个经历让田文昌至今想起来“内心很愧疚”。那是来自山东的一个女子来北京告状,听说田文昌之后找到了他所在的政法大学。因为田出差在外,那位女子便带着铺盖卷在楼道里吃睡,两天两夜没走。“我是夜里11点下的飞机,12点到家后,见到了她,她反反复复就两句话:‘田教授救救我。’‘我听说公检法都归你管。’看得出她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了,一打听原来是她哥哥在村里有几百块钱对不上。我跟她说,我给你几百块,你赶紧回去吧,她死活不答应。我回家她就要跟回去,没办法我只好打110。”那位女青年被送上车后,拼命砸车,无奈之中只好送到派出所收容。“我和爱人半夜2点才回去,始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又实在无能为力。”“媒体有时把我包装成包青天,实际上我不是,也不应该是这种角色。”
一篇介绍田文昌的文章称其为“敢打硬仗的律师”。为公众熟悉的事件有代理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集团诉讼案等。近几年,田文昌屡屡与那些“重量级”的诉讼联系在一起: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沈阳刘涌“涉黑案”、“福布斯富豪杨斌案”等。田文昌说,从本意上讲,其实很多案子“根本不愿意接”。“我愿意接那些律师发挥余地大的案子,有的案子牵涉的背景太多,往往付出几倍努力,得到的结果却只有几分之一。”但也正是那些牵涉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权力斗争的案件,最终找到田文昌。
在现实的中国法治环境下,即便称得上“功成名就”的田文昌说自己体会作为律师的“无力感”的时候不是“有没有”、而是“太多太多”。一位法律界人士评价说,虽然有时看起来即便有田文昌出马,也难改变什么,“但如果没有他,更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在采访田文昌时,断断续续有电话打来希望田文昌谈一下刚刚一审被判18年的杨斌一案,田文昌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眼下,田文昌正在等着另一个结果是一审被判死刑的沈阳刘涌一案的二审宣判。
“这个案子办得很苦,越办越后悔。”田文昌半开玩笑地说。刘涌案最初找到田文昌时,也被他拒绝了,“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需要靠这些案件出名”,但出于种种原因还是接了。与田文昌代理的其他几个案件相似,刘涌的案子一做又是三年,“其间几次反复,但是既然接手了,就要负责到底”。
2001年,刘涌案一审开庭,当天的场面让田文昌印象深刻:因为被告刘涌在当地的影响非同一般,沈阳警方出动了警犬来做安全检查,带着步话机的警察严阵以待,22个被告戴着头套被带上法庭。
“刘涌请来京城有名的大律师为其作辩护”的消息也早为人知,田文昌说他四处一望,“到处是敌意的目光,好像我就是第二个刘涌”。休息期间,有许多参加庭审者想接近他,跟他说话,全部被隔开,“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孤立”。刘涌案一审一共进行了10天,田文昌针对取证过程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等问题进行了辩护。等到最后一天,他感觉到“周围的目光也有了180度的改变”。第一个发言结束后,离开法庭时,8位公诉人全部起身,与田文昌一一握手,法院和检察院都表示希望田有机会给他们讲课。
从个人来说,田文昌无疑是成功的,但对其另一个角色——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则坦承“不能说自己是成功的”。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评价自己,田文昌自我检讨的成分占了主要部分。“没有市场意识是我的失误”,田文昌一脸坦诚。作为个人,田文昌“没有开拓的客观需求”是不难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拥有60多位员工的律师事务所的当家人,这无疑是个缺陷。
采访中,田文昌数次用“小作坊”一词,“中国的律师没有传统,律师的主流机制是各自为战”。田文昌说自己在建所开始就追求理想化的模式,但现实是“京都所的经济效益并没有和它所拥有的名气相对应”。
田文昌戏称自己是“啃骨头啃出了名,肉却没吃到多少”——在中国,做刑事辩护的费用低,而主动找上门来的不少案子都属于这类“出力不讨好”的案子。作为“京城名状”,田文昌的身价自然是外界关心的话题。对此,田文昌坦然应之:“我们的收费是可能比别人高”,但贵在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
“刘涌案被指控有53项犯罪事实,难度相当于100个案件还不止。且决非外界传闻的那样,两个律师干了3年收的费用并不多。有人说收了几百万,反正我没有见到过。”
看得出田文昌对京都所的前景依然自信。他说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全方位开拓业务”。田文昌最近也在积极联系一些国外业务,他毫不讳言这完全是从经营角度出发的。他一定要把“京都”办成一个集诉讼和非诉于一体,国内业务与涉外业务都堪称一流的全方位服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田文昌是个标准的成功人士,惟一的儿子在英国上学,应属衣食无忧。“我要是挣钱不是这么个挣法。”他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每天处心积虑地就是在想怎么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
“年轻时我那么多爱好,现在全扔了。我就是个工作机器,不唱歌不跳舞不消费,你说我图什么?沽名钓誉,我也没那个必要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律师应该算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功绩很大,但也只能是铺路石。也不是说我有多高尚,只是这些事情必须得有人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陈卫东是与田文昌相熟十几年的朋友,他说在法律圈里,尊重田的人多,“恨他咬牙切齿的人也不少”。“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你如果牺牲了,中国的法治也进步了。他也说,他随时准备着。”
其他70篇纪实文章:
>>返回 知名律师纪实 目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