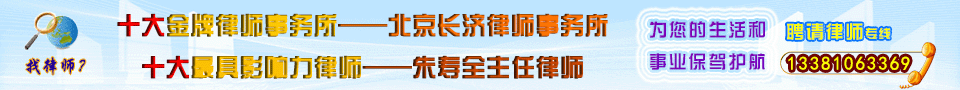实践中,“送子归案”、“大义灭亲”等观念仍然被不少人所赞美和提倡。这种立法与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案与惩治犯罪,却容易牺牲人类最美好的亲情关系。
假设在一漆黑的夜晚,有一亲人敲开您的门告诉您他杀了人,并要在您这儿躲几天。您是答应他?还是将他冷冷地推出门或者直接报警?再假设您明知您的亲人犯了案,警察在向您取证时,您是向警察作假证?还是如实向警察提供证明?
对每一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个两难选择。选择前者,将面临包庇罪的追究;选择后者,将受良心的自责和人性的拷问。无疑,在包庇罪的设置上,国法和人情出现了背离。
在欧洲历史上,有一国王曾规定:盗窃者的妻或子,如果不揭发这个盗窃罪行,就降为奴隶。孟德斯鸠抨击说,这项法律是违反人性的。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贝卡里亚也认为:“立法者用一只手束紧家庭、亲戚和朋友间的关系,另一只手却悬赏破坏和扯断这些关系的人。一向自相矛盾的立法者,一方面把人猜疑的心灵引向信任,另一方面却在大家心中挑拨离间。它不是在预防犯罪,相反,倒是在增加犯罪。”一、因过分重视打击犯罪,忽视亲情等社会价值,是我国在包庇罪设置上缺失近亲属间免证特权的根源。
在当代许多国家,法律赋予近亲属之间有免证特权。因为亲情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致立法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关系重大的证据。
然而,我们一直过分重视打击犯罪,忽视了亲情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为了表“忠心”,多少人与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划清界限,甚至主动相互揭发。这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伤痕至今仍然难以愈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法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忽视亲情的意识依然存在。一是刑法上包庇罪的不合理设置,二是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间免证特权的缺失。实践中,“送子归案”、“大义灭亲”等观念仍然被不少人所赞美和提倡。司法人员为了侦破案件,也常常从亲属身上寻找突破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庭成员间的恩爱与和谐,哪有社会的和谐?在建设和谐社会,尊重人性的时代背景下,包庇罪的罪状设置有修改的必要。
包庇罪在我国现在并不能废除,但是,包庇罪的罪状有进行更为科学和人性化改动的必要。尤其是发生在近亲属间的“相隐”问题。在遇到此种问题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别动辄将人之常情弃之不顾。应逐步引进证人不对其近亲属的罪行作证的规则。
然而,我国立法中却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即使是亲人间也不存在例外。这种立法规范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案与惩治犯罪,但却牺牲了人类最美好的亲情关系,在亲属间制造了怨恨,埋下了家庭不和谐的种子。
允许证人不对其近亲属的罪行作证的规则,自古以来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而我国现在却无类似规则。赋予具有近亲属身份证人拒绝作证权,有利于增进人们互爱互信、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平衡利益冲突、使刑事诉讼顺应人伦常理。
二、让亲人出庭作证有悖人伦,且使法的价值间发生严重冲突。
我国审判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最大程度的查清事实,证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此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但是,众所周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和谐与安定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亲属之爱是人类感情联系的基础,在亲属之爱与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法律能强迫有感情的人置亲情于不顾吗?
先贤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汉律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自此历朝历代法律以告发者与被告发者之亲属关系远近来衡量处罚,即关系越远处罚越轻,关系越近处罚越重,这也是儒家“亲亲相隐”司法化的体现。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属于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很难将其理解为一种“权利”,但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拒证权。我国历来家国一体,家和万事兴。强迫有直系亲属关系人员出庭作证,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势必使其心理产生重大的痛苦或逆反心理,对法律规定其作证义务产生反感,进而产生憎恨法律的情绪,不利于对法律的遵守和信仰,同时直系亲属之间相互指证,不利家庭和睦,最终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
证人的拒证权,似乎和我国一贯的诉讼原则不相符合。因为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默许相隐而且鼓励相隐。在今天规定这一制度,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法治的最大特征应当是使人成其为人,法应当具有人性基础”。所以,我国的证据制度不应排斥容隐制度,因为亲亲相隐(亦称容隐权)“在法律中的确立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它不但不违背世界法律之发展,而且为我们这样一个情味浓浓的社会所急需”。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通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们把其称为特权。这种规则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
在证据法的价值中,至少有四项基本价值,即秩序、个人自由、公平和效率。从我国现行的诉讼立法来看,我们过于注重公平与秩序以及效率,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保护,《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不考虑亲情的存在,就是实证之一。
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孟德斯鸠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
三、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是证人特权规则,世界上很多国家确立了这一证据规则,我国应吸取成功的且富有人性的法律适用制度。
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是证人特权规则之一,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拒绝充当本案证人或对本案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刑事诉讼规则。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亲亲相隐”规则。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现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未盲目抛弃这一传统,确立了近亲拒绝作证刑事规则,而且该规则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几乎都有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规定。如美国《1999年统一证据规则》第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作对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免权。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被告的近亲属没有义务作证。 但是当他们提出控告告诉或申请时或者他们的近亲属受到犯罪侵害时,应作证。法官应告知上述人员有权回避,并且询问他们是否行使此权利。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85条规定: 如果证人的证言可能引起本人或下列的人被提起公诉或被判有罪等有关身心耻辱的事项时,证人可以拒绝提作证:证人的亲族、户主、家族或曾经有过此类关系的人;证人的监护人或被证人监护的人。
古今中外的法治者们不约而同立法确认近亲之间的容隐,虽然各自的立法意图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看到认同近亲之间的容隐可以遏止或减少司法权运行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然而,我国现行刑事法规却没有赋予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述规定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排除于适用对象范围,其适用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证人因服从法律被迫牺牲亲情和家庭和谐关系,作不利亲人之证,而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和良心折磨的煎熬。二是证人为维护本人和家人的利益铤而走险作伪证包庇亲人而使自己也受到刑事惩罚,追诉一个犯罪却又造就一个新的犯罪,一个刑事诉讼却又催生另一个刑事案件。三是,证人迫不得已对抗法律,拒不履行作证义务,使法律的尊严被严重亵渎,导致法律权威降低。不论出现上述何种情况,都必将冲击社会的普遍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使人们对司法权和法律产生抵触情绪,于社会秩序安定及社会关系和谐不利。
因此,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无需特立独行,而有必要确立近亲拒绝作证刑事规则。
四、建立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就人权而言,“人权这一概念所指的主要是,一切人对于政府而言享有的权利。换句话说,人权主要是指政府对于一切人所承担的义务。人权主要是用来限制政府、约束政府、要求政府作某些行为,不作某些行为、使承担某些义务的概念。”倘若政府非但不履行应尽义务保护人权,反而漠视人权,其会严重腐蚀社会,毒化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让人们感到不履行义务、无视他人权利是“正常”现象,不履行义务,侵犯他人权利将蔚然成风。在此情形下,社会不可能有安定与和谐。因此,可以说近亲拒绝作证规则的确立,是加强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近亲拒绝作证规则能维护人们享有的人权中的家庭关系权、不受无明文规定之刑罚权、思想、良心自由权、不自证其罪权。
总之,就同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而论,它们之间应当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它们不应是对立的,即不应为法律所反对却为道德所支持,或反过来,为道德所反对却为法律所支持。固然一定的法律与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一定的法律制度所遵从,抑或所要维系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伦理道德观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尽管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在许多方面已不同于最早创设近亲容隐制度的汉唐和古罗马时代,然而对家庭成员的关爱、忠实、信任仍是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所极力倡导的主要内容,不过去除了封建的不平等的宗法思想。当今社会,支撑近亲拒绝作证规则的理论基础不仅有植根于永恒的人性之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观,还有由现代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所构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正义不能不包含我们这个时代伦理道德正义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