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148-law.com | English Version 联系律师 聘请律师 法律咨询 招聘律师 意见建议 友情链接 收藏本页 本站导航 | |
 www.148-law.com | English Version 联系律师 聘请律师 法律咨询 招聘律师 意见建议 友情链接 收藏本页 本站导航 | |
首页>>律师成长之路>>中国律师现状
| |||||||||||||||||||||||||||||||||||||||||||||||||||||||||||||||||||||||||||||||||||||||||||||||||||||||||||||||||||||||||||||||||||||||||||||||||||||||||||||||||||||||||||||||||||||||||||||||||||||||||||||||||||||||||||||||||||||||||||||||||||||||||||||||||||||||
| 年份 | 常年法律顾问万个 | 代写法律文书万件 | 法律咨询万件 | 非诉讼法律事务万件 | 刑事诉讼及代理 | 民事、经济 诉讼代理 |
行政诉讼 代理 |
||||
| 总数(万件) | 法院指定辩护(万件) | 被告委托辨护(万件) | 总数(万件) | 经济案(万件) | 总数(万件) | 代理原告(万件) | |||||
| 1985 | 3.94 | 31.64 | 163.55 | 4.55 | 10.7 | 0.76 | 9.94 | 10.82 | |||
| 1986 | 4.32 | 32.89 | 159.02 | 4.57 | 13.7 | 0.99 | 12.71 | 16.3 | 6.81 | ||
| 1987 | 5.95 | 41.59 | 190.38 | 6.04 | 15.45 | 1.22 | 14.23 | 20.86 | 9.62 | ||
| 1988 | 8.81 | 53.49 | 241.14 | 8 | 17.02 | 1.29 | 15.58 | 26.53 | 11.19 | ||
| 1989 | 10.88 | 56.84 | 262.58 | 14.78 | 23.24 | 1.76 | 21.48 | 32.93 | 21.13 | ||
| 1990 | 11.06 | 52.4 | 274.14 | 11.95 | 25.75 | 缺 | 缺 | 33.35 | 12.8 | ||
| 1991 | 12.89 | 275.11 | 244.19 | 23.67 | 23.1 | 19.5 | 9.7 | 22.69 | 1.73 | 1.43 | 0.53 |
| 1992 | 15.15 | 61.01 | 277.53 | 27.7 | 21.97 | 1.44 | 18.03 | 39.63 | 18.2 | 1,61 | 1.02 |
| 1993 | 18.57 | 60.02 | 241.48 | 35.04 | 19.17 | 1.29 | 15.5 | 48.33 | 23.71 | 1.53 | 0.99 |
| 1994 | 20.33 | 52.81 | 290.72 | 40.35 | 20.88 | 1.45 | 16.74 | 54.16 | 27.67 | 1.63 | 1.04 |
| 1995 | 23.45 | 54.38 | 196 | 45.2 | 20.44 | 1.5 | 15.64 | 64.12 | 32.49 | 1.8 | 1.09 |
| 1996 | 22.3 | 52.29 | 186.46 | 43.55 | 24.59 | 2.03 | 18.19 | 71.41 | 36.02 | 1.94 | 1.1 |
| 1997 | 23.24 | 95.87 | 42.52 | 122.22 | 27.52 | 2.27 | 14.78 | 85.76 | 40.33 | 2.96 | 1.75 |
资料来源:根据1987~1998年《中国法律年鉴》有关统计数字整理而成。说明:1.数字采取四舍五入原则,取小数点后两位数。
2.1989年4月4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自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因此相关的数字从1991年始。3.《中国法律年鉴》1990年前的统计是分列“非诉讼案件”和“涉外法律事务”两项,本表合并为“非诉讼法律事务”。
对于上表的统计数字,我想从业务的绝对量和相对于社会对律师服务的需求这样两个方面作一点分析。
从业务绝对量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各类业务在绝对数都有了程度不同的增长。以1993年为例,各类律师业务量较之于1985年,其增幅依次是:非诉讼法律事务670.1%,常年法律顾问371.3%,民事、经济诉讼代理346.7%,代写法律文书89.7%,刑事诉讼及代理79.2%,法律咨询47.6%。各种业务的平均增幅是267.4%,此外还新辟了行政诉讼代理业务。当然,1993年律师总数是68834人,较之于1985年的18000人,增幅为282.4%,与业务总量的平均增幅大致相当。其二,刑事辩护业务的起伏徘徊与民事、经济诉讼代理业务的迅猛增长以及非诉讼法律业务的不断攀高形成强烈反差。尽管刑事辩护业务在1991-1993年连跌三年后,于1994年开始回升,并于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7.52万件,但是,与此前最高的1990年的25.75万件比,增加仅6.87%。而1997年民事、经济诉讼代理业务,比1990年增加155.29%。与6.87%的增幅相比,1997年律师人数(79161人)比1990年律师人数(51200人)却增加54.61%——由于1997年律师人数是当年通过年检的数字,如果以1996年律师人数(100200人)来比,则比1990年增加95.7%。从律师业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上述反差虽说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刑事诉讼已日益成为律师业务兴盛的一块旧有的“基地”,但是,在它们那里出现的刑事诉讼业务萎缩都是在此业务充分发达之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其他律师业务而言的。相形之下,中国律师业还处于不高的发展水平,此时出现刑事诉讼业务的萎缩,除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外,律师业职业精神的缺乏和商业化气息过浓也是重要的原因。
律师业务绝对量的增加和增长的不平衡,说明了律师作用在绝对量上的增大,以及作用在不同领域发挥的不平衡。那么,中国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程度如何呢?换言之,律师业务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律师服务的需求了呢?很显然,律师业务在绝对数上的不同程度增长与对律师服务需求的满足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不断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断言,实际生活中律师服务需求量的增加要比律师业务的增长幅度大得多。在刑事案件、无财产内容或诉讼标的小的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找律师难问题,虽然能从这些类案件可获得的成就感较差、收费少等原因加以解释,但是在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太多的法律服务需求可供律师“择优”选择、挑肥捡瘦。
那么,在客观上对律师服务的需求量究竟有多大呢?在律师已有的业务量与这种需求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要有一个综合的衡量和评介尺度。这里,我打算从诉讼的角度,就1986年至1993年法院各类案件一审收案数、检察机关批捕或公诉人数与律师相应业务的开展数量通过表格作一比较,以便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上述问题。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所有的诉讼事务都要由律师来代理(何况中国法律也没有这样的垄断要求),而只是表明在客观上存在着那么一些潜在需求。
1986—1993年律师诉讼业务需求分析
| 年份 | 刑事诉讼 | 民事、经济诉讼 | 行政诉讼 | ||||
| 法院一审收案(万件)) | 检察机关批捕、公诉(万人 | 律师辩护及代理(万件) | 法院一审收案(万件) | 律师代理(万件) | 法院一审收案(万件) | 律师代理原告(万件) | |
| 1986 | 29.97 | 35.56 | 13.7 | 131.16 | 16.3 | ||
| 1987 | 28.96 | 35.71 | 15.45 | 158.04 | 20.86 | ||
| 1988 | 31.33 | 42.21 | 17.02 | 196.87 | 26.53 | 0.86 | |
| 1989 | 39.26 | 58 | 23.24 | 251.1 | 32.93 | 0.99 | |
| 1990 | 45.97 | 63.66 | 25.75 | 244.41 | 33.35 | 1.3 | |
| 1991 | 42.78 | 55.05 | 23.1 | 244.82 | 22.69 | 2.57 | |
| 1992 | 42.3 | 52.04 | 21.97 | 260.1 | 39.63 | 2.71 | 1.02 |
| 1993 | 40.33 | 50.57 | 19.17 | 298.55 | 48.33 | 2.79 | 0.99 |
| 合计 | 300.9 | 392.8 | 159.4 | 1785.05 | 240.62 | 11.22 | 2.01 |
资料来源:根据1987—1994年《中国法律年鉴》有关统计数字整理而成。说明:检察机关批捕或公诉一栏中,1989年以前为批准决定逮捕人数,以后为公诉人数,事实上,逮捕人数与公诉人数相差无几。
对于上表的数字,我们可以略作分析。先看刑事诉讼一栏。法院一审所收案子由公诉和刑事自诉(90至93年分别为7.38万件、8.01万件、9.24万件和8.59万件)两部构成,同时,收案数与当事人数也不是一回事,即使以一案双方两个当事人计算,后者也应该高于前者;而就律师辩护及代理来说,基本为一个当事人构成一件。因此,我们在列举了法院一审收案数的同时,列上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公诉的人数。表中所列的律师辩护及代理数是一个总数,假定只把它们看作是刑事一审的辩护及代理数,那么平均算来,它们是历年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或公诉人数的40.6%,是历年法院一审收案数的52.97%。由此也可以推测,实际上的刑事辩护率要远远低于这个百分比(据研究约20%)。就民事、经济诉讼而言,如果按照一案双方两代理的计算方法,那么律师代理民事、经济诉讼当事人的比率平均起来是6.74%左右。行政诉讼中律师代理原告的比率平均是17.91%。考虑到律师代理民事、经济诉讼数和行政诉讼数也是一个总数,实际上的代理率也必然远比6.74%和17.91%为低。这里,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数。例如,1992年和1993年中国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是158.27万件和161.69万件,检察机关自侦立案是7.85万件和7.29万件。假如考虑到律师业务在刑事侦查阶段的开展情况,那么现实生活中潜在的律师服务需求将更为巨大。
因此,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法治进程以来,社会变革使得律师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由于各种人为和客观的原因,这种作用的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
三.问题及观念成因:以刑事辩护为例
律师服务领域的拓展主要是在非诉讼领域,从律师业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律师从事的是非讼事务,但是,律师的“看家绝活”是诉讼业务。律师业所必备的捍卫法治、为民众服务的职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诉讼业务来支撑的。律师的地位是否提高,作用是否增大,诉讼是一个最基本的评价尺度。而在诉讼中,刑事辩护则更能反映律师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于1996年对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修改。这些修改强化了被刑事追究者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辩护地位,体现了围绕控、辩、审三方关系而形成的更为民主、合理的诉讼结构,因而使得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包括律师辩护制度)在整体更为完善。具体地说,这种进步不仅表现在令世人瞩目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提前介入”上,而且还表现在为保证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以及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制定并不断完善的各种措施上。例如,在法律援助(包括援助的主体、对象、范围、形式,援助机构和基金的建立,申请援助的程序等)、律师履行职责的保障(包括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和联络,查阅、摘抄、复制有关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调查取证等)、律师的职业技能和伦理等方面,中国在规则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的趋势。
但是,在为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拍案喝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的局限性以及与有关国际标准的差距,不能不正视它在实施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目前人们尤其是律师议论最多的问题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律师庭前阅卷难、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难,以及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不欢迎、排斥、刁难,甚至侵犯律师的人身权利和辩护权利。甚至在新刑法和新刑诉法实施后,由于对所规定的律师伪证罪缺乏严格界定,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执业风险增大。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用的发挥。
联系上文所提及的律师刑事辩护业务不发达和萎缩的现象,应该说中国律师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难以让人满意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是在各种人为因素中对律师刑事辩护在观念认识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不解决这些观念上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律师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际问题妥善解决,在整体上也难以改变对律师功能的制度预设和社会预期,从而严重制约律师作用的发挥。
1.信奉实事求而非无罪推定。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辩护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辩护权制度的确立,则是为实现公平审判而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不彻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就不可能在一种充分的意义上被规定和实现。许多人认为,1996年刑诉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因为该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其实不然,对此只要简单比照一下国际人权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可资说明。《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一项规定:“凡受刑事追究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这里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的表述为“不得确定有罪”,后者的表述是“有权被视为无罪”。从逻辑上说,“不得确定有罪”也就同时意味着“不得确定无罪”,因而所体现的还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实事求是原则。按照参与刑诉法修改者的解释,1996年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立法原意是为了废除检察院免予起诉制度,保证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它并不意味着彻底吸纳无罪推定原则。
2.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及其对律师作用的不利影响。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对这一原则的规范含义细加分析,并考察它们被实施的实况,那么就可以发现,它在普遍意义上促成了刑事诉讼中三机关并驾齐驱的态势,使它们成为刑事诉讼职能的承担者,成为刑事诉讼过程的操纵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封闭格局。中国律师制度是在70年代末重建的,律师对刑事诉讼的介入以及律师作用的强化,无异于在这种既成的封闭格局中契入一种新的因素,从而必然对总体平衡造成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律师的作用必然在很长时期里受到既定格局的“排异”限制。这种限制加上缺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随着律师失去对国家权力的依托,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向“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的转变,将更为严峻。
3.对律师立场、作用的怀疑。中国律师生存在不利的法律文化传统之中(“无讼”、“贱讼”、 “讼师”、“讼棍”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被刑事追究者视同罪犯,把律师辩护看作是“为罪犯说话”,“没有立场”。这种观念尽管目前已有根本改变,但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由于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尚属初步,职业伦理规范还不健全,也影响了其整体的社会公信度。
4.对侦查阶段刑事辩护意义认识不足。侦查阶段获得律师辩护帮助的意义在于,案件的决定性证据可能在这一阶段产生,如果此时缺乏法定有效的辩护帮助,就可能会严重损害被刑事追究者的辩护权和司法公正。对此,人们显然认识不足。
5.对刑事追究机关的“追究”偏向在制度设计上认识不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这一原则的体现,刑诉法第89条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应当“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这一规定尽管没错,但却蕴涵着一种观念,即人们一般总是倾向于认为,侦查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权的机关,只要无私心私情干扰,就能够以事实为重,秉公办案。这显然是一种为常识所蒙蔽的想法。其实,侦查机关作为追究犯罪的机关,虽然与被追究者不存在个人恩怨,但由于它们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它们往往会偏向于“追究者”的立场。因此,要求它们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的规定固然必要,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停留于泛泛,而不进一步通过强化辩护权等作出制度上的制约和防范,就不足以纠偏,不足以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人权。
(原载陈景良主编:《中南法律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张志铭:《法理思考的印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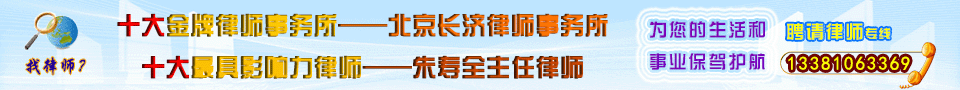 |
|
聘请律师Beijing Changji Law Offic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在线律师》版权所有 English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