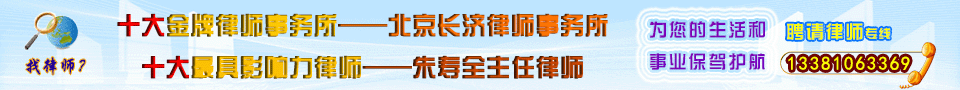大律师王工记
《记者观察》乔思远
http://www.21gwy.com/wz/2203/a/0553/490553.html
【“王工律师是一位老律师。他的‘老’,实因他对中国律师业的贡献、他对中国律师前途命运的关切、奔走、劳作……”——《中国律师》原总编刘桂明
“中国律师(王工)一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就以十分高大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中国青年报》《红旗》《半月谈》
“王工不死,服务不止……哪怕(法制建设)只前进一厘米,我都非常高兴。” ——王工
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
第一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即席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发出“民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的历史性诘问(1988年);
第一个提出《律师法》立法议案,建议建立完善的律师制度(1988年)……】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但是工字上面不出头,所以我不能为士,成不了硕士、博士,当不了大学者;工字下面不出头,我也当不了官。”
北京房山,上午8点,外面春光明媚。王工笑得慈眉善目,与记者通过报道所想像的严肃冷峻大有不同。老人两鬓花白,带着浓重湖南味的男高音依然洪亮,“愚见”“老朽”“没有读过多少书”等语句中透露出的谦逊、平和,让人很难和他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振臂一呼、他办案时的不服权贵、他提出民间对日索赔时的坚韧执着、他的《黑洞》中律师的原型联系起来。
记者要给他和老伴照合影,他指着身上稍显破旧的棉袄问:“这个行不行啊?”然后连声呼唤妻子:“老婆,老婆过来,合影了。”
王工的老伴说,如果不是和记者约好采访事宜,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轧马路”。暖和无风的时候,王工也会找球友打打乒乓球,除此之外,他的嗜好就是读书、著文、打官司了。
坎坷的前半生
1929年,王工诞生于湖南沅江,这是位于洞庭湖畔的一个小地方。当时的王工叫兆晃,兆晃的童年生活充斥着饥饿与流浪。八九岁时日本军队轰炸了王工的家乡,从此,他过上了逃亡、饥饿的生活。
11岁时,父母双双亡故,这种苦难也造就了他的坚强。兆晃的学业是靠半工半读支撑下去的,上完高小教初小,上完初中教高小,上完高中教初中。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使他于1947年踉踉跄跄地升入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教育专业。
此时,兆晃的“反骨”开始显露。刚开始他非常珍惜读书机会,准备一心一意读书。然而,“我不找政治,政治却找我。”“兵荒马乱的中国,放不下我一张书桌。”战争期间,学校里的教育资源少得可怜,也学不到多少知识。由于学校经常克扣青年学生的口粮,兆晃和同窗整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本来不是规矩的学生。”而“兆晃”两字在南方方言与“造反”谐音,于是当局就怀疑兆晃是“共党”。兆晃和同窗们早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不满,同时又亲身体验着被克扣口粮以致饿肚子的痛苦,他们真的开始闹起了学潮。
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汉。一天早上,就在华中师范大学和他兼课的克强中学门外,满眼都是解放军。“他们都很自律,宁愿睡在街上也不惊扰我们,和国民党军真是不一样啊。”
20岁的兆晃“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决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了表达对革命的忠诚,他把名字兆晃改为王工,并立刻放弃学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在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后12兵团一部组建人民海军,王工随即去了当时的海军基地青岛,几个月后到北京担任《人民海军》的编辑、记者。
1953年,王工因“不能证明自己的历史是非常清白的”,所以从《人民海军》调到了基层的一个速成中学教书。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作为没有“老实交待个人问题”的王工被调离了京城,转业到安徽的蚌埠市委工作,在蚌埠市委的《整风通讯》中担任编辑和记者。
1958年,他被押解到合肥南边的白湖劳动教养。当时的白湖还是万顷碧波,王工和其他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白湖的水排干,实现“沧海变良田”的大跃进。从1958年年末到1962年的几年中,他们不管春夏秋冬,在湖水里面劳动、吃饭、大小便。
王工当时干活很上心,“特别舍得掏力气。”有次“放了卫星”,他得到了一大盆米饭的奖励,他连水都没喝,也不就菜,“扒拉几下就扒拉完了。那盆有足足洗脸盆大,现在我一个星期也吃不完啊。”至今让王工念念不忘的一次“美食”经历是有次他干完活休息时,竟发现了一窝白花花的鸡蛋,“敲烂了蛋壳直接就吞到嘴里,味道实在太好了。”
如今的王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更多的是豁达,“我现在快80了,身体好得很呢,我要感谢反‘右派’斗争啊,感谢当‘右派’让我有个好身体。”他笑称当年同在安徽白湖劳教过的战友为“白大同学”。
1963年,王工被甄别平反了,然而劫难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以“老右派”的身份关进了牛棚。
律师的律师
王工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他真正作为专业律师的时间不过10年多。从1979年恢复自由算起,到1989年离休,10年的时间,王工从“被动当律师”终于成为一代著名的律师。
1979年,王工的“春天终于来了”,他可以“过有饭吃,有工作做的幸福生活了”。就在这一年,中国最为重要的两部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我国的法制建设初露曙光。
当时正在安徽某中学当语文教师的王工被调配到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在此之前,王工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律。在1980年前后像王工一样走上法律岗位的人非常多,因为在当时律师也属公职人员。
王工初到法院并没有直接接触法律,也不懂得何谓实体法和程序法。当时他在法院的司法科工作,主要负责纠正案例卷宗中的文字错误。“当时的判决书老是闹笑话,错字不少,语句也不通顺。”由于法学教材匮乏,也就是靠着一点点看卷宗,他开始学习法律知识。这个时候,王工已经50岁了,“都说年过半百不学艺,我50岁了,从来没有受过科班的正规训练,却开始改行。”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人才奇缺。以当时的蚌埠市为例,只有两个律师,后来也不过三五个人,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律师都要“一锅端”。遇到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案件,只能抠政策,讲道理,甚至把建国前解放区的司法经验、调解经验都用到法律实践当中。
当时的王工以敢接“胡子案”“骨头案”而闻名。由于办案经验多了,他担任了安徽省淮河修防局的法律顾问。不久,王工被聘为水利部顾问,把国内主要河流流经的省份全跑遍了,各个地方的案子他都办过。由于水利工程涉及到民房搬迁、各个省份的水源分配等,纠纷多,官司复杂,当时律师比较少,“胆子大,又说真话,人称‘水律师’,找我的人特别多,就出名了。”
1988年,王工即将离休,就在这一年,他由安徽省人大代表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成了安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王工在人代会上的表现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律师身份。
1988年,王工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在会上,他以不同凡响的4次即席发言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以他洪亮的男高音4次起身发表意见,把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中国青年报》)“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红旗》杂志)
王工坦言,他对当官、出风头并无兴趣,但是他既然当了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人民,之所以敢于冲破“文革”后的人代会上的沉默,就是想到职责所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是渎职,是对责任和义务的背叛。”
当人大代表5年间,王工共提出各种议案300多条,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提出议案最多的人之一。其中大部分涉及立法、冤案纠正、律师权益保护等,有的已经得到落实。
“民大还是官大,权大还是法大?我们的口号:人民万岁!宪法神圣!”他喊出了热情的口号,并一直为曾两次被违法逮捕的辽宁台安3律师奔波呼号。该案被彭真称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宪事件”,也被业界人士认为是我国律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84年,律师王百义、王力成、王志双因进行刑事辩护,被违法逮捕,其中王力成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著名律师张思之为之辩护,冤案直到1988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而作为第一个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为3位律师鸣不平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王工的肩上。
也许正是体会到了律师执业环境的艰难,就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王工提出了219号议案,建议制定《律师法》。正是在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律师法》得以顺利起草、通过,并最终在1997年正式实施。
当记者问王工作为第一个即席发言的代表为何敢于“吃螃蟹”时,他这样说:“我国的‘官本位’思想历来比较严重,就拿开会来说,每个人在发言时心里其实是有潜在的‘名单’的,往往是按照官位大小排出先后顺序,官大的先发言,平民百姓靠后站。但对于我这个人大代表,人代会上是我唯一重要的表达意见的机会。”
为了能够在人代会上抢到发言机会,幸运地被排在前面坐的王工,每次开会都是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
1989年离休之后,王工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律师权益的维护,王工编写了两部关于律师权益维护的书籍,分别是《中国律师涉案实录》和《为中国律师抗辩》;第二个是领衔提出民间对日索赔,出版了专著《对日索赔》等4部书籍。
领衔提出民间对日索赔
1988年夏天,王工收到了一封从湖北十堰寄来的信。来信人是李固平,他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王工谈到了中国在被日本侵略期间所受到的奇耻大辱。
“我国政府已经于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利,但是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并不会因为政府放弃索赔而自动消失。”王工看到这封信后久久难以平静,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颠沛流离、不知饱暖的苦难生活,而全中国又有多少像他一样甚至比他更惨的战争受害者呢?
工作之余,王工开始致力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为了提交对日索赔议案,1991年,他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化工大学附近,天天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时值冬天,“特别冷的天,风刮得呼呼的,顶风的时候,车子刮得直往后退。”
之前的王工几乎没有接触过国际法,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他看了几百万字的相关历史资料、法律法规,整理了一摞沉甸甸的草稿。这份议案得到了其他代表的广泛认同,共有36名全国人大代表在议案上签名以示支持。
1992年3月18日上午8点,王工推开了全国人代会大会议案组的门,将有关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和百份建议提交大会。这份名为《建议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共同社抢先播发,美国等一些国家均全文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外交部发言人等先后针对该议案所涉及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离休之后,王工和老伴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房山区,间或到广东、安徽等地出差。他的书房里摆着一个小床,床上的纺绸被子已经陈旧得褪了色,但却非常洁净,剩下的空间都被书填满了。记者看到他的一摞摞已经发黄变脆的旧案卷,里面的字迹是那么工整。正如律师顾世伟对王工的评论:“本人对于整部《论语》的概括,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字:无倦!对于王工律师,我也要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其精神:无倦!”
作为全国著名的律师,王工的孩子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奋斗过日子,儿子、女儿都是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我不会去找关系、托人情去给他们捞什么好处,好坏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王工现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看书、著文,他笑称现在终于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我的生活不规律,饿了就吃啊,困了就睡。有时候夜里醒来,脑子里有灵感了,爬起来就写。”
年轻十来岁的老伴说王工很好照料,“做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挑食。”王工从来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我不管钱的事,反正我每个月现在是两千多的退休金,够花了。”
老伴常常说他“很笨”,王工也自称“没为家里的事操过心,主要是操也操不好”。一辈子都没挣到多少钱的王工,安徽的房子已不存在,他现在居住的位于北京房山区的小房子是亲友们给操办的。
眼下王工最关注的就是安徽蚌埠市施徐村的拆迁案,这个案子曾得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批示,可被拆迁人仍未得到合理的补偿。为这个案子奔波,完全是王工和另一位律师彭金钊以公民身份无偿代理的,因为被拆迁人都是农民,已经无家可归,“穷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不能不管。”由于年事已高,现在的王工力求从理论上对解决拆迁问题有所帮助,他正在论证1991年出台、2001年修订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涉嫌违宪。他说:“如果这个意见得到立法机构重视,那么全国的拆迁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了。拆迁现在成了社会焦点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事,出大事。”他写了几篇关于拆迁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在了废纸的空白处,誊抄得干干净净。
一生坎坷,然王工少有戚戚之忧:“安徽的案子是拖了好几年都没解决,但只要我尽力了就好。不如意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要是天天心忧气躁,世上早就没王工了。”
“不管如何,毕竟,从纵向上来看,我国的法治进程是朝着正面走的。”华发苍颜的王工笑的一瞬间,如此纯真。